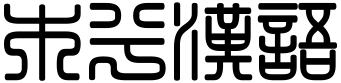-
[宋代] 苏轼
臣等猥以空疏,备员讲读。圣明天纵,学问日新。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,心欲言而口不逮,以此自愧,莫知所为。
窃谓人臣之纳忠,譬如医者之用药,药虽进于医手,方多传于古人。若已经效于世间,不必皆从于己出。
伏见唐宰相陆贽,才本王佐,学为帝师。论深切于事情,言不离于道德。智如子房而文则过,辩如贾谊而术不疏,上以格君心之非,下以通天下之志。但其不幸,仕不遇时。德宗以苛刻为能,而贽谏之以忠厚;德宗以猜疑为术,而贽劝之以推诚;德宗好用兵,而贽以消兵为先;德宗好聚财,而贽以散财为急。至于用人听言之法,治边驭将之方,罪己以收人心,改过以应天道,去小人以除民患,惜名器以待有功,如此之流,未易悉数。可谓进苦口之乐石,针害身之膏肓。使德宗尽用其言,则贞观可得而复。
臣等每退自西阁,即私相告言,以陛下圣明,必喜贽议论。但使圣贤之相契,即如臣主之同时。昔冯唐论颇、牧之贤,则汉文为之太息;魏相条、董之对,则孝宣以致中兴。若陛下能自得师,莫若近取诸贽。夫六经三史,诸子百家,非无可观,皆足为治。但圣言幽远,末学支离,譬如山海之崇深,难以一二而推择。如贽之论,开卷了然。聚古今之精英,实治乱之龟鉴。臣等欲取其奏议,稍加校正,缮写进呈。愿陛下置之坐隅,如见贽面,反覆熟读,如与贽言。必能发圣性之高明,成治功于岁月。臣等不胜区区之意,取进止。
-
[宋代] 苏轼
敕。朕式观古初,灼见天意。将有非常之大事,必生希世之异人。使其名高一时,学贯千载。智足以达其道,辩足以行其言。瑰玮之文,足以藻饰万物;卓绝之行,足以风动四方。用能于期岁之闲,靡然变天下之俗。
具官王安石,少学孔、孟,晚师瞿、聃。罔罗六艺之遗文,断以己意;糠秕比百家之陈迹,作新斯人。属熙宁之有为,冠群贤而首用。信任之笃,古今所无。方需功业之成,遽起山林之兴。浮云何有,脱屣如遗。屡争席于渔樵,不乱群于麋鹿。进退之美,雍容可观。
朕方临御之初,哀疚罔极。乃眷三朝之老,邈在大江之南。究观规模,想见风采。岂谓告终之问,在予谅暗之中。胡不百年,为之一涕。于戏。死生用舍之际,孰能违天;赠赙哀荣之文,岂不在我。宠以师臣之位,蔚为儒者之光。庶几有知,服我休命。可。
-
[宋代] 苏轼
孔子曰:「刚毅木讷,近仁。」又曰:「巧言令色,鲜矣仁。」所好夫刚者,非好其刚也,好其仁也。所恶夫佞也,非恶其佞也,恶其不仁也。吾平生多难,常以身试之,凡免我于厄者,皆平日可畏人也;挤我于俭者,皆异时可喜人也。吾是以知刚者之必仁,佞者之必不仁也。
建中靖国之初,吾归自海南,见故人,问存没,追论平生所见刚者,或不幸死矣。若孙君介夫讳立节者,真可谓刚者也。始吾弟子由为条例司属官,以议不合引去。王荆公谓君曰:「吾条例司当得开敏如子者。」君笑曰:「公言过矣,当求胜我者。若我辈人,则亦不肯为条例司矣。」公不答,径起入户,君亦趋出。君为镇江军书记,吾时通守钱塘,往来常、润间,见君京口。方新法之初,监司皆新进少年,驭吏如束湿,不复以礼遇士大夫,而独敬惮君,曰:「是抗丞相不肯为条例司者。」
谢麟经制溪洞事宜,州守王奇与蛮战死,君为桂州节度判官,被旨鞠吏士之有罪者。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,且尽斩之。君持不可。麟以语侵君。君曰:「狱当论情,吏当守法。逗挠不进,诸将罪也。既伏其辜矣,馀人可尽戮乎!若必欲以非法斩人,则经制司自为之,我何与焉。」麟奏君抗拒,君亦奏麟侵狱事。刑部定如君言,十二人皆不死,或以迁官。吾以是益知刚者之必仁也。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于必死乎!
方孔子时,可谓多君子,而曰「未见刚者」,以明其难得如此。而世乃曰「太刚则折!」士患不刚耳,长养成就,犹恐不足,当忧其太刚而惧之以折耶!折不折,天也,非刚之罪。为此论者,鄙夫患失者也。
-
[宋代] 苏轼
予昔为密州,殿中丞刘庭式为通判。庭式,齐人也。而子由为齐州掌书记,得其乡闾之言以告予,曰:「庭式通礼学究。未及第时,议娶其乡人之女,既约而未纳币也。庭式及第,其女以疾,两目皆盲。女家躬耕,贫甚,不敢复言。或劝纳其幼女。庭式笑曰:『吾心已许之矣。虽盲,岂负吾初心哉!』卒娶盲女,与之偕老。」盲女死于密,庭式丧之,逾年而哀不衰,不肯复娶。予偶问之:「哀生于爱,爱生于色。子娶盲女,与之偕老,义也。爱从何生,哀从何出乎?」庭式曰:「吾知丧吾妻而已,有目亦吾妻也,无目亦吾妻也。吾若缘色而生爱,缘爱而生哀,色衰爱驰,吾哀亦忘。则凡扬袂倚市,目挑而心招者,皆可以为妻也耶?」予深感其言,曰:「子功名富贵人也。」或笑予言之过,予曰:「不然,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,霸叛入蜀,亲友皆告绝,而叔子独安其室,恩礼有加焉。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贵也,其后卒为晋元臣。今庭式亦庶几焉,若不贵,必且得道。」时坐客皆怃然不信也。昨日有人自庐山来,云:「庭式今在山中,监太平观,面目奕奕有紫光,步上下峻阪,往复六十里如飞,绝粒不食,已数年矣。此岂无得而然哉!」闻之喜甚,自以吾言之不妄也,乃书以寄密人赵杲卿。杲卿与庭式善,且皆尝闻余言者。庭式,字得之,今为朝请郎。杲卿,字明叔,乡贡进士,亦有行义。元丰六年七月十五日,东坡居士书。
-
[宋代] 苏轼
尝读《孔子世家》,观其言语文章,循循莫不有规矩,不敢放言高论,言必称先王,然后知圣人忧天下之深也。茫乎不知其畔岸,而非远也;浩乎不知其津涯,而非深也。其所言者,匹夫匹妇之所共知;而所行者,圣人有所不能尽也。呜呼!是亦足矣。使后世有能尽吾说者,虽为圣人无难,而不能者,不失为寡过而已矣。
子路之勇,子贡之辩,冉有之智,此三者,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。然三子者,每不为夫子之所悦。颜渊默然不见其所能,若无以异于众人者,而夫子亟称之。且夫学圣人者,岂必其言之云尔哉?亦观其意之所向而已。夫子以为后世必有不能行其说者矣,必有窃其说而为不义者矣。是故其言平易正直,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,要在于不可易也。
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,既而焚灭其书,大变古先圣王之法,于其师之道,不啻若寇仇。及今观荀卿之书,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,而不足怪也。
荀卿者,喜为异说而不让,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。其言愚人之所惊,小人之所喜也。子思、孟轲,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。荀卿独曰:“乱天下者,子思、孟轲也。”天下之人,如此其众也;仁人义士,如此其多也。荀卿独曰:“人性恶。桀、纣,性也。尧、舜,伪也。”由是观之,意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,而自许太过。彼李斯者,又特甚者耳。
今夫小人之为不善,犹必有所顾忌,是以夏、商之亡,桀、纣之残暴,而先王之法度、礼乐、刑政,犹未至于绝灭而不可考者,是桀、纣犹有所存而不敢尽废也。彼李斯者,独能奋而不顾,焚烧夫子之六经,烹灭三代之诸侯,破坏周公之井田,此亦必有所恃者矣。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,以自是其愚,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。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时之论,而荀卿亦不知其祸之至于此也。
-
[宋代] 苏轼
余谪居惠州,子由在高安,各以一子自随,馀分寓许昌、宜兴,岭海隔绝。诸子不闻余耗,忧愁无聊。苏州定慧院学佛者卓契顺谓迈曰:“子何忧之甚,惠州不在天上,行即到耳,当为子将书问之。”
绍圣三年三月二日,契顺涉江度岭,徒行露宿,僵仆瘴雾,黧面茧足以至惠州,得书径还。余问其所求,答曰:“契顺惟无所求而后来惠州;若有所求,当走都下矣。”苦问不已,乃曰:“昔蔡明远鄱阳一校耳,颜鲁公绝粮江淮之间,明远载米以周之。鲁公怜其意,遗以尺书,天下至今知有明远也。今契顺虽无米与公,然区区万里之勤,傥可以援明远例,得数字乎?”余欣然许之。独愧名节之重,字画之好,不逮鲁公,故为书渊明《归去来辞》以遗之,庶几契顺托此文以不朽也。
-
[宋代] 苏轼
君子可以寓意于物,而不可以留意于物。寓意于物,虽微物足以为乐,虽尤物不足以为病。留意于物,虽微物足以为病,虽尤物不足以为乐。老子曰:“五色令人目盲,五音令人耳聋,五味令人口爽,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。”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,亦聊以寓意焉耳。刘备之雄才也,而好结髦。嵇康之达也,而好锻炼。阮孚之放也,而好蜡屐。此岂有声色臭味也哉,而乐之终身不厌。
凡物之可喜,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,莫若书与画。然至其留意而不释,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。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,宋孝武、王僧虔至以此相忌,桓玄之走舸,王涯之复壁,皆以儿戏害其国凶此身。此留意之祸也。
始吾少时,尝好此二者,家之所有,惟恐其失之,人之所有,惟恐其不吾予也。既而自笑曰:吾薄富贵而厚于书,轻死生而重于画,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?自是不复好。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,然为人取去,亦不复惜也。譬之烟云之过眼,百鸟之感耳,岂不欣然接之,然去而不复念也。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。
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在戚里,而其被服礼义,学问诗书,常与寒士角。平居攘去膏粱,屏远声色,而从事于书画,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,以蓄其所有,而求文以为记。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,故以是告之,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。
熙宁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记。
-
[宋代] 苏轼
轼启。远蒙差人致书问安否,辅以药物,眷意甚厚。自二月二十五日,至七月十三日,凡一百三十余日乃至,水陆盖万余里矣。罪戾远黜,既为亲友忧,又使此二人者,跋涉万里,比其还家,几尽此岁,此君爱我之过而重其罪也。但喜比来侍奉多暇,起居佳胜。
轼罪大责薄,居此固宜,无足言者。瘴疠之邦,僵仆者相属于前,然亦皆有以取之。非寒暖失宜,则饥饱过度,苟不犯此者,亦未遽病也。若大期至,固不可逃,又非南北之故矣。以此居之泰然。不烦深念。
前后所示著述文字,皆有古作者风力,大略能道此意欲言者。孔子曰:“辞达而已矣。”辞至于达,止矣,不可以有加矣。《经说》一篇诚哉是言也。西汉以来,以文设科而文始衰,自贾谊、司马迁,其文已不逮先秦古书,况所谓下者。文章犹尔,况其道德者乎?
若所论周勃,则恐不然。平、勃未尝一日忘汉,陆贾为之谋至矣。彼视禄、产犹几上肉,但将相和调,则大计自定。若如君言,先事经营,则吕后觉悟,诛两人,而汉亡矣。
轼少时好议论,既老,涉世更变,往往悔其言之过,故乐以此告君也。儒者之病,多空言而少实用。贾谊、陆贾文学,殆不传于世。老病且死,独欲以此教子弟,岂意姻亲中,乃有王郎乎?
-
[宋代] 苏轼
天可必乎?贤者不必贵,仁者不必寿。天不可必乎?仁者必有后。二者将安取衷哉?吾闻之申包胥曰:“人定者胜天,天定亦能胜人。”世之论天者,皆不待其定而求之,故以天为茫茫。善者以怠,恶者以肆。盗跖之寿,孔、颜之厄,此皆天之未定者也。松柏生于山林,其始也,困于蓬蒿,厄于牛羊;而其终也,贯四时,阅千岁而不改者,其天定也。善恶之报,至于子孙,则其定也久矣。吾以所见所闻考之,而其可必也,审矣。国之将兴,必有世德之臣,厚施而不食其报,然后其子孙,能与守文太平之主,共天下之福。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,显于汉、周之际,历事太祖、太宗,文武忠孝,天下望以为相,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。葢尝手植三槐于庭,曰:“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。”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,相真宗皇帝于景德、祥符之闲。朝廷清明,天下无事之时,享其福禄荣名者,十有八年。
今夫寓物于人,明日而取之,有得有否;而晋公修德于身,责报于天,取必于数十年之后,如持左契,交手相付。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。吾不及见魏公,而见其子懿敏公,以直谏事仁宗皇帝,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,位不满其德。天将复兴王氏也欤?何其子孙之多贤也!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,其雄才直气,真不相上下。而栖筠之子吉甫,其孙德裕,功名富贵,略与王氏等,而忠恕仁厚,不及魏公父子。由此观之,王氏之福,葢未艾也。懿敏公之子巩,与吾游,好德而文,以世其家。吾是以录之。铭曰:
呜呼休哉!
魏公之业,与槐俱萌;封植之勤,必世乃成。
既相真宗,四方砥平。归视其家,槐阴满庭。
-
[宋代] 苏轼
夫当今生民之患,果安在哉?在于知安而不知危,能逸而不能劳。此其患不见于今,而将见于他日。今不为之计,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。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,是故天下虽平,不敢忘战。秋冬之隙,致民田猎以讲武,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,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,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。是以虽有盗贼之变,而民不至于惊溃。及至后世,用迂儒之议,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,天下既定,则卷甲而藏之。数十年之后,甲兵顿弊,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,卒有盗贼之警,则相与恐惧讹言,不战而走。开元、天宝之际,天下岂不大治?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,豢于游戏酒食之间,其刚心勇气,销耗钝眊,痿蹶而不复振。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,四方之民,兽奔鸟窜,乞为囚虏之不暇,天下分裂,而唐室固以微矣。
盖尝试论之:天下之势,譬如一身。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,岂不至哉?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。至于农夫小民,终岁勤苦,而未尝告病。此其故何也?夫风雨、霜露、寒暑之变,此疾之所由生也。农夫小民,盛夏力作,而穷冬暴露,其筋骸之所冲犯,肌肤之所浸渍,轻霜露而狎风雨,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。今王公贵人,处于重屋之下,出则乘舆,风则袭裘,雨则御盖。凡所以虑患之具,莫不备至。畏之太甚,而养之太过,小不如意,则寒暑入之矣。是以善养身者,使之能逸而能劳;步趋动作,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;然后可以刚健强力,涉险而不伤。夫民亦然。今者治平之日久,天下之人骄惰脆弱,如妇人孺子,不出于闺门。论战斗之事,则缩颈而股栗;闻盗贼之名,则掩耳而不愿听。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,以为生事扰民,渐不可长。此不亦畏之太甚,而养之太过欤?
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。愚者见四方之无事,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,此亦不然矣。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二虏者,岁以百万计。奉之者有限,而求之者无厌,此其势必至于战。战者,必然之势也。不先于我,则先于彼;不出于西,则出于北。所不可知者,有迟速远近,而要以不能免也。天下苟不免于用兵,而用之不以渐,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,一旦出身而蹈死地,则其为患必有不测。故曰:天下之民,知安而不知危,能逸而不能劳,此臣所谓大患也。
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,讲习兵法;庶人之在官者,教以行阵之节;役民之司盗者,授以击刺之术。每岁终则聚于郡府,如古都试之法,有胜负,有赏罚。而行之既久,则又以军法从事。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,又挠以军法,则民将不安,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。天下果未能去兵,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。夫无故而动民,虽有小怨,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?
今天下屯聚之兵,骄豪而多怨,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,何故?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,惟我而已。如使平民皆习于兵,彼知有所敌,则固以破其奸谋,而折其骄气。利害之际,岂不亦甚明欤?
-
[宋代] 苏轼
太史公论《诗》,以为“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,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”。以余观之,是特识变风,变雅耳,乌睹《诗》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,然后变风发乎情,虽衰而未竭,是以犹止于礼义,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。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,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!古今诗人众矣,而杜子美为首,岂非以其流落饥寒,终身不用,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。
今定国以余故得罪,贬海上三年,一子死贬所,一子死于家,定国亦病几死。余意其怨我甚,不敢以书相闻。而定国归至江西,以其岭外所作诗数百首寄余,皆清平丰融,蔼然有治世之音,其言与志得道行者无异。幽忧愤叹之作,盖亦有之矣,特恐死岭外,而天子之恩不及报,以忝其父祖耳。孔子曰:“不怨天,不尤人。”定国且不我怨,而肯怨天乎!余然后废卷而叹,自恨期人之浅也。
又念昔日定国遇余于彭城,留十日,往返作诗几百馀篇,余苦其多,畏其敏,而服其工也。一日,定国与颜复长道游泗水,登桓山,吹笛饮酒,乘月而归。余亦置酒黄楼上以待之,曰:“李太白死,世无此乐三百年矣。”
今余老,不复作诗,又以病止酒,闭门不出。门外数步即大江,经月不至江上,眊眊焉真一老农夫也。而定国诗益工,饮酒不衰,所至翱翔徜徉,穷山水之胜,不以厄穷衰老改其度。今而后,余之所畏服于定国者,不独其诗也。
-
[宋代] 苏轼
曷尝观于富人之稼乎?其田美而多,其食足而有余。其田美而多,则可以更休,而地力得全;其食足而有余,则种之常不后时,而敛之常及其熟。故富人之稼常美,少秕而多实,久藏而不腐。
今吾十口之家,而共百亩之田。寸寸而取之,日夜以望之,锄、铚 、耰、艾,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,而地力竭矣。种之常不及时,而敛之常不待其熟。此岂能复有美稼哉?
古之人,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。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,以待其成者,闵闵焉,如婴儿之望之长也。弱者养之,以至于刚;虚者养之,以至于充。三十而后仕,五十而后爵。信于久屈之中,而用于至足之后;流于既溢之余,而发于持满之末。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,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。
吾少也有志于学,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,吾子之得,亦不可谓不早也。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,而众已妄推之矣。呜呼!吾子其去此,而务学也哉!博观而约取,厚积而薄发,吾告子止于此矣。
子归过京师而问焉,有曰辙、子由者,吾弟也,其亦以是语之。
-
[宋代] 苏轼
浮扁舟以适楚兮,过屈原之遗宫。览江上之重山兮,曰惟子之故乡。伊昔放逐兮,渡江涛而南迁。去家千里兮,生无所归而死无以为坟。悲夫!人固有一死兮,处死之为难。徘徊江上欲去而未决兮,俯千仞之惊湍。赋《怀沙》以自伤兮,嗟子独何以为心。忽终章之惨烈兮,逝将去此而沉吟。
“吾岂不能高举而远游兮,又岂不能退默而深居?独嗷嗷其怨慕兮,恐君臣之愈疏。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,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。苟宗国之颠覆兮,吾亦独何爱于久生。托江神以告冤兮,冯夷教之以上诉。历九关而见帝兮,帝亦悲伤而不能救。怀瑾佩兰而无所归兮,独惸乎中浦。”
峡山高兮崔嵬,故居废兮行人哀。子孙散兮安在,况复见兮高台。自子之逝今千载兮,世愈狭而难存。贤者畏讥而改度兮,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。黾勉于乱世而不能去兮,又或为之臣佐。变丹青于玉莹兮,彼乃谓子为非智。
“惟高节之不可以企及兮,宜夫人之不吾与。违国去俗死而不顾兮,岂不足以免于后世?”
呜呼!君子之道,岂必全兮。全身远害,亦或然兮。嗟子区区,独为其难兮。虽不适中,要以为贤兮。夫我何悲?子所安兮。
-
[宋代] 苏轼
古今画水,多作平远细皱,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,使人至以手扪之,谓有漥隆,以为至妙矣。然其品格,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。
唐广明中,处士孙位始出新意,画奔湍巨浪,与山石曲折,随物赋形,尽水之变,号称神逸。其后蜀人黄筌、孙知微皆得其笔法。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,营度经岁,终不肯下笔。一日,苍黄入寺,索笔墨甚急,奋袂如风,须臾而成,作输泻跳蹙之势,汹汹欲崩屋也。知微既死,笔法中绝五十余年。
近岁成都人蒲永升,嗜酒放浪,性与画会,始作活水,得二孙本意,自黄居窠兄弟、李怀衮之流,皆不及也。王公富人或以势力使之,永升辄嘻笑舍去。遇其欲画,不择贵贱,顷刻而成。尝与予临寿宁院水,作二十四幅,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,即阴风袭人,毛发为立。永升今老矣,画亦难得,而世之识真者亦少。如往日董羽、近日常州戚氏画水,世或传宝之。如董、戚之流,可谓死水,未可与永升同年而语也。
元丰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,黄州临皋亭西斋戏书。
-
[宋代] 李清照
慧则通,通则无所不达;专则精,精则无所不妙。故庖丁之解牛,郢人之运斤,师旷之听,离娄之视。大至于尧舜之仁,桀纣之恶;小至于掷豆起蝇,巾角拂棋,皆臻至理者何?妙而已。
后世之人,不惟学圣人之道,不到圣处。虽嬉戏之事,亦得依稀仿佛而遂止者多矣。夫博者无他,争先术耳。故专者能之。予性喜博,凡所谓博者皆耽之,昼夜每忘寝食,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?精而已。
自南渡来流离迁徙,尽散博具,故罕为之。然实未尝忘于胸中也。今年冬十月朔,闻淮上警报,江浙之人,自东走西,自南走北;居山林者谋入城市,居城市者谋入山林,旁午络绎,莫卜所之。易安居士亦自临安溯流,涉严滩之险,抵金华,卜居陈氏第。乍释舟楫而见轩窗,意颇释然。更长烛明,奈此良夜乎?于是乎博弈之事讲矣,且长行、叶子、博塞、弹棋,是无传者。打揭、大小、猪窝、族鬼、胡画、数仓、睹快之类,皆鄙俚,不经见。藏酒、摴蒲、双蹙融,近渐废绝。选仙、加减、插关火,质鲁任命,无所施人智巧。大小象戏、奕棋,又惟可容二人。独采选、打马,特为闺房戏。
长恨采选丛繁,劳于检阅,故能通者少,难遇勍敌。打马简要,而苦无文采。按打马世有两种:一种一将十马者,谓之关西马;一种无将二十马者,谓之依经马。流行既久,各有图经凡例可考。行移赏罚,互有同异。又宣和间,人取两种马,参杂加减,大约交加彻幸,古意尽矣,所谓宣和马者是也。予独爱依经马,因取其赏罚互度,每事做数语,随事附见,使儿辈图之。不独施之博徒,实足贻诸好事,使千万世后,知命辞打马,始自易安居士是也。
绍兴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,易安室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