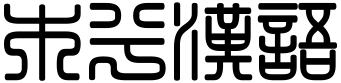-
[宋代] 苏轼
元祐六年十月,颍州久旱,闻颍上有张龙公神祠,极灵异,乃斋戒遣男迨与州学教授陈履常往祷之。迨亦颇信道教,沐浴斋居而往。明日,当以龙骨至,天色少变。二十六日,会景贶、履常、二欧阳,作诗云:“后夜龙作云,天明雪填渠。梦回闻剥啄,谁呼赵、陈、予?”景贶拊掌曰:“句法甚亲,前此未有此法。”季默曰:“有之。长官请客吏请客,目曰‘主簿、少府、我’。即此语也。”相与笑语。至三更归时,星斗灿然,就枕未几,而雨已鸣檐矣。至朔旦日,作五人者复会于郡斋。既感叹龙公之威德,复喜诗语之不谬。季默欲书之,以为异日一笑。是日,景贶出迨诗云:“吾侪归卧髀骨裂,会友携壶劳行役。”仆笑曰:“是男也,好勇过我。”
-
[宋代] 苏轼
轼启:新岁未获展庆,祝颂无穷,稍晴起居何如?数日起造必有涯,何日果可入城。昨日得公择书,过上元乃行,计月末间到此,公亦以此时来,如何?窃计上元起造,尚未毕工。轼亦自不出,无缘奉陪夜游也。沙枋画笼,旦夕附陈隆船去次,今先附扶劣膏去。此中有一铸铜匠,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,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。或令看过,因往彼买一副也。乞蹔付去人,专爱护便纳上。余寒更乞保重,冗中恕不谨,轼再拜。季常先生文阁下。正月二日。
子由亦曾言,方子明者,他亦不甚怪也。得非柳中舍已到家言之乎,未及奉慰疏,且告伸意,伸意。柳丈昨得书,人还即奉谢次。知壁画已坏了,不须怏怅。但顿着润笔新屋下,不愁无好画也。
-
[宋代] 苏轼
黄州山水清远,土风厚善,其民寡求而不争,其士静而文,朴而不陋。虽闾巷小民,知尊爱贤者,曰:“吾州虽远小,然王元之、韩魏公,尝辱居焉。”以夸于四方之人。元之自黄迁蕲州,没于蕲,然世之称元之者,必曰黄州,而黄人亦曰“吾元之也”。魏公去黄四十馀年,而思之不忘,至以为诗。夫贤人君子,天下之所以遗斯民,天下之所共有,而黄人独私以为宠,岂其尊德乐道,独异于他邦也欤?抑二公与此州之人,有宿昔之契,不可知也?元之为郡守,有德于民,民怀之不忘也固宜。魏公以家艰,从其兄居耳,民何自知之?《诗》云:“有匪君子,如金如锡,如圭如璧。”金锡圭璧之所在,瓦石草木被其光泽矣,何必施于用?奉议郎孙贲公素,黄人也,而客于公。公知之深,盖所谓教授书记者也。而轼亦公之门人,谪居于黄五年,治东坡,筑雪堂,盖将老焉,则亦黄人也。于是相与摹公之诗而刻之石,以为黄人无穷之思。而吾二人者,亦庶几托此以不忘乎?元丰七年十月二十六日,汝州团练副使苏轼记。
-
[宋代] 苏轼
叶嘉,闽人也。其先处上谷。曾祖茂先,养高不仕,好游名山,至武夷,悦之,遂家焉。尝曰:「吾植功种德,不为时采,然遗香后世,吾子孙必盛于中土,当饮其惠矣。」茂先葬郝源,子孙遂为郝源民。
至嘉,少植节操。或劝之业武。曰:「吾当为天下英武之精,一枪一旗,岂吾事哉!」因而游见陆先生,先生奇之,为著其行录传于时。方汉帝嗜阅经史时,建安人为谒者侍上,上读其行录而善之,曰:「吾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!」曰:「臣邑人叶嘉,风味恬淡,清白可爱,颇负其名,有济世之才,虽羽知犹未详也。」上惊,敕建安太守召嘉,给传遣诣京师。
郡守始令采访嘉所在,命赍书示之。嘉未就,遣使臣督促。郡守曰:「叶先生方闭门制作,研味经史,志图挺立,必不屑进,未可促之。」亲至山中,为之劝驾,始行登车。遇相者揖之,曰:「先生容质异常,矫然有龙凤之姿,后当大贵。」
嘉以皂囊上封事。天子见之,曰:「吾久饫卿名,但未知其实尔,我其试哉!」因顾谓侍臣曰:「视嘉容貌如铁,资质刚劲,难以遽用,必槌提顿挫之乃可。」遂以言恐嘉曰:「砧斧在前,鼎镬在后,将以烹子,子视之如何?」嘉勃然吐气,曰:「臣山薮猥士,幸惟陛下采择至此,可以利生,虽粉身碎骨,臣不辞也。」上笑,命以名曹处之,又加枢要之务焉。因诫小黄门监之。有顷,报曰:「嘉之所为,犹若粗疏然。」上曰:「吾知其才,第以独学未经师耳。嘉为之,屑屑就师,顷刻就事,已精熟矣。」
上乃敕御史欧阳高、金紫光禄大夫郑当时、甘泉侯陈平三人与之同事。欧阳疾嘉初进有宠,曰:「吾属且为之下矣。」计欲倾之。会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,欧但热中而已,当时以足击嘉,而平亦以口侵陵之。嘉虽见侮,为之起立,颜色不变。欧阳悔曰:「陛下以叶嘉见托,吾辈亦不可忽之也。」因同见帝,阳称嘉美而阴以轻浮訿之。嘉亦诉于上。上为责欧阳,怜嘉,视其颜色,久之,曰:「叶嘉真清白之士也。其气飘然,若浮云矣。」遂引而宴之。
-
[宋代] 苏轼
方今天下何病哉!其始不立,其卒不成,惟其不成,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。凡人之情,一举而无功则疑,再则倦,三则去之矣。今世之士,所以相顾而莫肯为者,非其无有忠义慷慨之志也,又非其才术谋虑不若人也,患在苦其难成而不复立。不知其所以不成者,罪在于不立也。苟立而成矣。
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,其所从起者,则五六十年矣。自宫室祷祠之役兴,钱币茶盐之法坏,加之以师旅,而天下常患无财。五六十年之间,下之所以游谈聚议,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,不可胜数矣,而财终不可丰。自澶渊之役,北虏虽求和,而终不得其要领,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,而边陲不宁,二国益骄。以战则不胜,以守则不固,而天下常患无兵。五六十年之间,下之所以游谈聚议,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,不可胜数矣,而兵终不可强。自选举之格严,而吏拘于法,不志于功名;考功课吏之法坏,而贤者无所劝,不肖者无所惧,而天下常患无吏。五六十年之间,下之所以游谈聚议,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择吏者,不可胜数矣,而吏终不可择。财之不可丰,兵之不可强,吏之不可择,是岂真不可耶?故曰:「其始不立,其卒不成,惟其不成,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。」
夫所贵于立者,以其规摹先定也。古之君子,先定其规摹,而后从事,故其应也有候,而其成也有形。众人以为是汗漫不可知,而君子以为理之必然,如炊之无不熟,种之无不生也。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。
昔者子太叔问政于子产。子产曰:「政如农功,日夜以思之,思其始而图其终,朝夕而行之,行无越思,如农之有畔。」子产以为不思而行,与凡行而出于思之外者,如农之无畔也,其始虽勤,而终必弃之。今夫富人之营宫室也,必先料其赀财之丰约,以制宫室之大小,既内决于心,然后择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,必告之曰:「吾将为屋若干,度用材几何?役夫几人?几日而成?土石材苇,吾于何取之?」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:「某所有木,某所有石,用材役夫若干,某日而成。」主人率以听焉。及期而成,既成而不失当,则规摹之先定也。
今治天下则不然。百官有司,不知上之所欲为也,而人各有心。好大者欲王,好权者欲霸,而偷者欲休息。文吏之所至,则治刑狱,而聚敛之臣,则以货财为急。民不知其所适从也。及其发一政,则曰姑试行之而已,其济与否,固未可知也。前之政未见其利害,而后之政复发矣。凡今之所谓新政者,听其始之议论,岂不甚美而可乐哉。然而布出于天下,而卒不知其所终。何则?其规摹不先定也。用舍系于好恶,而废兴决于众寡。故万全之利,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;百世之患,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。所用之人无常责,而所发之政无成效。此犹适千里不斋粮而假丐于涂人;治病不知其所当用之药,而百药皆试,以侥幸于一物之中。欲三患之去,不可得也。
-
[宋代] 苏轼
夫为国不可以生事,亦不可以畏事。畏事之弊,与生事均。譬如无病而服药,与有病而不服药,皆可以杀人。夫生事者,无病而服药也。畏事者,有病而不服药也。乃者阿里骨之请,人人知其不当予,而朝廷予之,以求无事,然事之起,乃至于此,不几于有病而不服药乎?今又欲遽纳夏人之使,则是病未除而药先止,其与几何。
-
[宋代] 苏轼
熙宁四年二月某日,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,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:
臣近者不度愚贱,辄上封章言灯事。自知渎犯天威,罪在不赦,席稿私室,以待斧钺之诛;而侧听逾旬,威命不至,问之府司,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,乃知陛下不惟赦之,又能听之。惊喜过望,以至感泣。何者?改过不吝,从善如流,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,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。顾此买灯毫发之失,岂能上累日月之明,而陛下幡然改命,曾不移刻,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,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。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,可与为汤武,可与富民而措刑,可与强兵而伏戎狄矣。有君如此,其忍负之!惟当披露腹心,捐弃肝脑,尽力所至,不知其它。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,有大于买灯者矣,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,盖未信而谏,圣人不与;交浅言深,君子所戒。是以试论其小者,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。今陛下果赦而不诛,则是既已许之矣;许而不言,臣则有罪;是以愿终言之。
臣之所欲言者三,愿陛下结人心,厚风俗,存纪纲而已。
人莫不有所恃,人臣恃陛下之命,故能役使小民;恃陛下之法,故能胜服强暴。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?书曰:“予临兆民,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。”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。聚则为君民,散则为仇雠。聚散之间,不容毫厘。故天下归往谓之王,人各有心谓之独夫。由此观之,人主之所恃者,人心而已。人心之于人主也,如木之有根,如灯之有膏,如鱼之有水,如农夫之有田,如商贾之有财。木无根则稿,灯无膏则灭,鱼无水则死,农无田则饥,商贾无财则贫,人主失人心则亡。此理之必然,不可逭之灾也。其为可畏,从古以然。苟非乐祸好亡,狂易丧志,则孰敢肆其胸臆,轻犯人心。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,赂伯石以安巨室,以为众怒难犯,专欲难成,而孔子亦曰:“信而后劳其民,未信则以为厉已也。”惟商鞅变法,不顾人心,虽能骤至富彊,亦以召怨天下。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,见刑而不见德,虽得天下,旋踵而失也;至于其身,亦卒不免负罪出走,而诸侯不纳,车裂以狥,而秦人莫哀。君臣之间,岂愿如此。宋襄公虽行仁义。失众而亡;田常虽不义,得众而强。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,先观众心之向背。谢安之用诸桓,未必是,而众之所乐,则国以乂安。庾亮之召苏峻,未必非,而势有不可,则反为危辱。自古及今,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,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。
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。中外之人,无贤不肖,皆言祖宗以来,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,经今百年,未尝阙事。今者无故又创一司,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。六七少年,日夜讲求于内;使者四十馀辈,分行营干于外。造端宏大,民实惊疑;创法新奇,吏皆惶惑。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,未免于忧;小人则以其意度朝廷,遂以为谤,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,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。商贾不行,物价腾踊,近自淮甸,远及川蜀,喧传万口,论说百端。或言京师正店,议置监官;夔路深山,当行酒禁;拘收僧尼常住;减刻兵吏廪禄;如此等类,不可胜言。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。斯言一出,民且狼顾。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,然而莫之顾者,徒曰“我无其事,又无其意,何恤于人言。”夫人言虽未必皆然,而疑似则有以致谤。人必贪财也,而后人疑其盗;人必好色也,而后人疑其淫。何者?未置此司,则无其谤,岂去岁之人皆忠厚,今岁之人皆虚浮?孔子曰: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”又曰:“必也正名乎。”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,有其名而辞其意,虽家置一喙以自解,市列千金以购人,人必不信,谤亦不止。夫制置三司条例司,求利之名也;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,求利之器也。驱鹰犬而赴林薮,语人曰:“我非猎也”,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;操网罟而入江湖,语人曰:“我非渔也”,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。故臣以为,消谗慝以召和气,复人心而安国本,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。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,不过以兴利除害也。使罢之而利不兴,害不除,则勿罢;罢之而天下悦,人心安,兴利除害,无所不可,则何苦而不罢?
-
[宋代] 苏轼
吾州之俗,有近古者三。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,其民尊吏而畏法,其农夫合耦以相助。盖有三代、汉、唐之遗风,而他郡之所莫及也。始朝廷以声律取士,而天圣以前,学者犹袭五代之弊,独吾州之士,通经学古,以西汉文词为宗师。方是时,四方指以为迂阔。至于郡县胥史,皆挟经载笔,应对进退,有足观者。而大家显人,以门族相上,推次甲乙,皆有定品,谓之江乡。非此族也,虽贵且富,不通婚姻。其民事太守县令,如古君臣,既去,辄画象事之,而其贤者,则记录其行事以为口实,至四五十年不忘。商贾小民,常储善物而别异之,以待官吏之求。家藏律令,往往通念而不以为非,虽薄刑小罪,终身有不敢犯者。岁二月,农事始作。四月初吉,谷稚而草壮,耘者毕出。数十百人为曹,立表下漏,鸣鼓以致众。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,一人掌鼓,一人掌漏,进退作止,惟二人之听。鼓之而不至,至而不力,皆有罚。量田计功,终事而会之,田多而丁少,则出钱以偿众。七月既望,谷艾而草衰,则仆鼓决漏,取罚金与偿众之钱,买羊豕酒醴,以祀田祖,作乐饮食,醉饱而去,岁以为常。其风俗盖如此。
故其民皆聪明才智,务本而力作,易治而难服。守令始至,视其言语动作,辄了其为人。其明且能者,不复以事试,终日寂然。苟不以其道,则陈义秉法以讥切之,故不知者以为难治。
今太守黎侯希声,轼先君子之友人也。简而文,刚而仁,明而不苟,众以为易事。既满将代,不忍其去,相率而留之,上不夺其请。既留三年,民益信,遂以无事。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筑之,作远景楼,日与宾客僚吏游处其上。轼方为徐州,吾州之人以书相往来,未尝不道黎侯之善,而求文以为记。
嗟夫,轼之去乡久矣。所谓远景楼者,虽想见其处,而不能道其详矣。然州人之所以乐斯楼之成而欲记焉者,岂非上有易事之长,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!孔子曰:「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。有马者借人乘之。今亡矣夫。」是二者,于道未有大损益也,然且录之。今吾州近古之俗,独能累世而不迁,盖耆老昔人岂弟之泽,而贤守令抚循教诲不倦之力也,可不录乎!若夫登临览观之乐,山川风物之美,轼将归老于故丘,布衣幅巾,从邦君于其上,酒酣乐作,援笔而赋之,以颂黎侯之遗爱,尚未晚也。
-
[宋代] 苏轼
故魏国忠献韩公,作堂于私第之池上,名之曰“醉白”。取乐天《池上》之诗,以为醉白堂之歌。意若有羡于乐天而不及者。天下之士,闻而疑之,以为公既已无愧于伊、周矣,而犹有羡于乐天,何哉?
轼闻而笑曰:公岂独有羡于乐天而已乎?方且愿为寻常无闻之人,而不可得者。天之生是人也,将使任天下之重,则寒者求衣,饥者求食,凡不获者求得。苟有以与之,将不胜其求。是以终身处乎忧患之域,而行乎利害之涂,岂其所欲哉!夫忠献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,浩然将归老于家,而天下共挽而留之,莫释也。当是时,其有羡于乐天,无足怪者。然以乐天之平生而求之于公,较其所得之厚薄浅深,孰有孰无,则后世之论,有不可欺者矣。文致太平,武定乱略,谋安宗庙,而不自以为功。急贤才,轻爵禄,而士不知其恩。杀伐果敢,而六军安之。四夷八蛮想闻其风采,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。此公之所有,而乐天之所无也。乞身于强健之时,退居十有五年,日与其朋友赋诗饮酒,尽山水园池之乐。府有余帛,廪有余粟,而家有声伎之奉。此乐天之所有,而公之所无也。忠言嘉谟,效于当时,而文采表于后世。死生穷达,不易其操,而道德高于古人。此公与乐天之所同也。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,亦不以其所无自少,将推其同者而自托焉。方其寓形于一醉也,齐得丧,忘祸福,混贵贱,等贤愚,同乎万物,而与造物者游,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。古之君子,其处己也厚,其取名也廉,是以实浮于名而世诵其美不厌。以孔子之圣而自比于老彭,自同于丘明,自以为不如颜渊。后之君子,实则不至,而皆有侈心焉。臧武仲自以为圣,白圭自以为禹,司马长卿自以为相如,扬雄自以为孟轲,崔浩自以为子房,然世终莫之许也。由此观之,忠献公之贤于人也远矣。
昔公尝告其子忠彦,将求文于轼以为记而未果。既葬,忠彦以告,轼以为义不得辞也,乃泣而书之。
-
[宋代] 苏轼
右《登彼公堂》四章,章四句,太守陈公之词也。
苏子曰:士之求仕也,志于得也,仕而不志于得者,伪也。苟志于得而不以其道,视时上下而变其学,曰:吾期得而已矣。则凡可以得者,无不为也,而可乎?昔者齐景公田,招虞人以旌,不至。孔子善之,曰:「招虞人以皮冠。」夫旌与皮冠,于义未有损益也,然且不可,而况使之弃其所学,而学非其道欤?
熙宁五年,钱塘之士贡于礼部者九人,十月乙酉,燕于中和堂,公作是诗以勉之曰:流而不返者,水也,不以时迁者,松柏也;言水而及松柏,于其动者,欲其难进也。万世不移者,山也,时飞时止者,鸿雁也;言山而及鸿雁,于其静者,欲其及时也。公之于士也,可谓周矣。《诗》曰:「无言不酬,无德不报。」二三子何以报公乎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