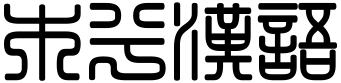-
[宋代] 司马光
起阏逢摄提格,尽昭阳大渊献,凡十年。
高皇后元年(甲寅,公元前一八七年)
冬,太后议欲立诸吕为王,问右丞相陵。陵曰:“高帝刑白马盟曰:‘非刘氏而王,天下共击之。’今王吕氏,非约也。”太后不说,问左丞相平、太尉勃,对曰:“高帝定天下,王子弟;今太后称制,王诸吕,无所不可。”太后喜,罢朝。王陵让陈平、绛侯曰;“始与高帝啑血盟,诸君不在邪?今高帝崩,太后女主,欲王吕氏;诸君纵欲阿意背约,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乎?”陈平、降侯曰:“于今,面折廷争,臣不如君;全社稷,定刘氏之后,君亦不如臣。”陵无以应之。十一月,甲子,太后以王陵为帝太傅,实夺之相权。陵遂病免归。乃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,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,不治事,令监宫中,如郎中令。食其故得幸于太后,公卿皆因而决事。太后怨赵尧为赵隐王谋,乃抵尧罪。上党守任敖尝为沛狱吏,有德于太后,乃以为御史大夫。太后又追尊其父临泗侯吕公为宣王,兄周吕令武侯泽为悼武王,欲以王诸吕为渐。
-
[宋代] 司马光
起玄黓摄提格,尽昭阳赤奋若,凡十二年。
太祖高皇帝下八年(壬寅,公元前一九九年)
冬,上东击韩王信馀寇于东垣,过柏人。贯高等壁人于厕中,欲以要上。上欲宿,心动,问曰:“县名为何?”曰:“柏人。”上曰:“柏人者,迫于人也。”遂不宿而去。十二月,帝行自东垣至。
-
[宋代] 司马光
起屠维大渊献,尽重光赤奋若,凡三年。
太祖高皇帝中五年(己亥,公元前二零二年)
冬,十月,汉王追项羽至固陵,与齐王信、魏相国越期会击楚;信、越不至,楚击汉军,大破之。汉王复坚壁自守,谓张良曰:“诸侯不从,奈何?”对曰:“楚兵且破,二人未有分地,其不至固宜。君王能与共天下,可立致也。齐王信之立,非君王意,信亦不自坚;彭越本定梁地,始,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,今豹死,越亦望王,而君王不早定。今能取睢阳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,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。信家在楚,其意欲复得故邑。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,使各自为战,则楚易破也。”汉王从之。于是韩信、彭越皆引兵来。
-
[宋代] 司马光
起强圉作噩,尽著雍阉茂,凡二年。
太祖高皇帝上之下三年(丁酉,公元前二零四年)
冬,十月,韩信、张耳以兵数万东击赵。赵王及成安君陈馀闻之,聚兵井陉口,号二十万。
-
[宋代] 司马光
起旃蒙协洽,尽柔兆涒滩,凡二年。
太祖高皇帝上之上元年(乙未,公元前二零六年)
冬,十月,沛公至霸上。秦王子婴素车、白马,系颈以组,封皇帝玺、符、节,降轵道旁。诸将或言诛秦王。沛公曰:“始怀王遣我,固以能宽容。且人已降,杀之不祥。”乃以属吏。
-
[宋代] 司马光
起昭阳大荒落,尽阏逢敦牂,凡二年。
二世皇帝下二年(癸巳,公元前二零八年)
冬,十月,泗川监平将兵围沛公于丰,沛公出与战,破之,令雍齿守丰。十一月,沛公引兵之薛。泗川守壮兵败于薛,走至戚,沛公左司马得杀之。
-
[宋代] 司马光
起阏逢阉茂,尽玄黓执徐,凡十九年。
始皇帝下二十年(甲戌,公元前二二七年)
荆轲至咸阳,因王宠臣蒙嘉卑辞以求见,王大喜,朝服,设九宾而见之。荆轲奉图以进于王,图穷而匕首见,因把王袖而揕之;未至身,王惊起,袖绝。荆轲逐王,王环柱而走。群臣皆愕,卒起不意,尽失其度。而秦法,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,左右以手共搏之,且曰:“王负剑!”负剑,王遂拔以击荆轲,断其左股。荆轲废,乃引匕首擿王,中铜柱。自知事不就,骂曰:“事所以不成者,以欲生劫之,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!”遂体解荆轲以徇。王于是大怒,益发兵诣赵,就王翦以伐燕,与燕师、代师战于易水之西,大破之。
-
[宋代] 司马光
起柔兆敦牂,尽昭阳作噩,凡二十八年。
昭襄王五十二年(丙午,公元前二五五年)
河东守王稽坐与诸侯通,弃市。应侯日以不怿。王临朝而叹,应侯请其故。王曰:“今武安君死,而郑安平、王稽等皆畔,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,吾是以忧。”应侯惧,不知所出。燕客蔡泽闻之,西入秦,先使人宣言于应侯曰:“蔡泽,天下雄辩之士。彼见王,必困君而夺君之位。”应侯怒,使人召之。蔡泽见应侯,礼又倨。应侯不快,因让之曰:“子宣言欲代我相,请闻其说。”蔡泽曰:“吁,君何见之晚也!夫四时之序,成功者去。君独不见夫秦之商君、楚之吴起、越之大夫种,何足愿与?”应侯谬曰:“何为不可?!此三子者,义之至也,忠之尽也。君子有杀身以成名,死无所恨!”蔡泽曰:“夫人立功岂不期于成全邪?身名俱全者,上也;名可法而身死者,次也;名僇辱而身全者,下也。夫商君、吴起、大夫种,其为人臣尽忠致功,则可愿矣。闳夭、周公,岂不亦忠且圣乎?!三子之可愿,孰与闳夭、周公哉?”应侯曰:“善。”蔡泽曰:“然则君之主惇厚旧故,不倍功臣,孰与孝公、楚王、越王?”曰:“未知何如。”蔡泽曰:“君之功能孰与三子?”曰:“不若。”蔡泽曰:“然则君身不退,患恐甚于三子矣。语曰:‘日中则移,月满则亏。’进退嬴缩,与时变化,圣人之道也。今君之怨已雠而德已报,意欲至矣而无变计,窃为君危之。”应侯遂延以为上客,因荐于王。王召与语,大悦,拜为客卿。应侯因谢病免。王新悦蔡泽计画,遂以为相国,泽为相数月,免。
-
[宋代] 司马光
起阏逢困敦,尽著雍困敦,凡二十五年。
赧王中十八年(甲子,公元前二九七年)
楚怀王亡归。秦人觉之,遮楚道。怀王从间道走赵。赵主父在代,赵人不敢受。怀王将走魏,秦人追及之,以归。
-
[宋代] 司马光
孟子曰:「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,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。」此王公大人之乐,非贫贱者所及也。孔子曰:「饭蔬(疏)食饮水,曲肱而枕之,乐在其中矣。」颜子「一箪食,一瓢饮」,「不改其乐」;此圣贤之乐,非愚者所及也。若夫「鹪鹩巢林,不过一枝;偃鼠饮河,不过满腹」,各尽其分而安之。此乃迂叟之所乐也。
熙宁四年迂叟始家洛,六年,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关,以为园。其中为堂,聚书出五千卷,命之曰读书堂。堂南有屋一区,引水北流,贯宇下,中央为沼,方深各三尺。疏水为五派,注沼中,若虎爪;自沼北伏流出北阶,悬注庭中,若象鼻;自是分而为二渠,绕庭四隅,会于西北而出,命之曰弄水轩。堂北为沼,中央有岛,岛上植竹,圆若玉玦,围三丈,揽结其杪,如渔人之庐,命之曰钓鱼庵。沼北横屋六楹,厚其墉茨,以御烈日。开户东出,南北轩牖,以延凉飔,前后多植美竹,为清暑之所,命之曰种竹斋。沼东治地为百有二十畦,杂莳草药,辨其名物而揭之。畦北植竹,方若棋局,径一丈,屈其杪,交桐掩以为屋。植竹于其前,夹道如步廊,皆以蔓药覆之,四周植木药为藩援,命之曰采药圃。圃南为六栏,芍药、牡丹、杂花,各居其二,每种止植两本,识其名状而已,不求多也。栏北为亭,命之曰浇花亭。洛城距山不远,而林薄茂密,常若不得见,乃于园中筑台,构屋其上,以望万安、轘辕,至于太室,命之曰见山台。
迂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,上师圣人,下友群贤,窥仁义之源,探礼乐之绪,自未始有形之前,暨四达无穷之外,事物之理,举集目前。所病者,学之未至,夫又何求于人,何待于外哉!志倦体疲,则投竿取鱼,执纴采药,决渠灌花,操斧伐竹,濯热盥手,临高纵目,逍遥相羊,惟意所适。明月时至,清风自来,行无所牵,止无所框,耳目肺肠,悉为己有。踽踽焉,洋洋焉,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。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。
或咎迂叟曰:「吾闻君子所乐必与人共之,今吾子独取足于己不及人,其可乎?」迂叟谢曰:「叟愚,何得比君子?自乐恐不足,安能及人?况叟之所乐者薄陋鄙野,皆世之所弃也,虽推以与人,人且不取,岂得强之乎?必也有人肯同此乐,则再拜而献之矣,安敢专之哉!
-
[宋代] 司马光
治平三年夏,苏府君终于京师,光往吊焉。二孤轼、辙哭且言曰:“今将奉先君之柩归葬于蜀。蜀人之祔也,同垄而异圹。日者吾母夫人之葬也,未之铭,子为我铭其圹。”因曰:“夫人之德,非异人所能知也,愿闻其略。”二孤奉其事状拜以授光。
光拜受,退而次之曰:夫人姓程氏,眉山大理寺丞文应之女,生十八年归苏氏。程氏富而苏氏极贫。夫人入门,执妇职,孝恭勤俭。族人环视之,无丝毫鞅鞅骄居可讥诃状,由是共贤之。或谓夫人曰:“父母非乏于财,以父母之爱,若求之,宜无不应者。何为甘此蔬粝,独不可以一发言乎?”夫人曰:“然。以我求于父母,诚无不可。万一使人谓吾夫为求于人以活其妻子者,将若之何?”卒不求。时祖姑犹在堂,老而性严,家人过堂下,履错然有声,已畏获罪。独夫人能顺适其志,祖姑见之必悦。
府君年二十七犹不学,一日慨然谓夫人曰:“吾自视,今犹可学。然家待我而生,学且废生,奈何?”夫人曰:“我欲言之久矣,恶使子为因我而学者!子苟有志,以生累我可也。”即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,不数年遂为富家。府君由是得专志于学,卒为大儒。夫人喜读书,皆识其大义。轼、辙之幼也,夫人亲教之,常戒曰:“汝读书,勿效曹耦,止欲以书生自名而已。”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厉之,曰:“汝果能死直道,吾亦无戚焉。”已而,二子同年登进士第,又同登贤良方正科。辙所对语尤切直惊人,由夫人素勖之也。
始夫人视其家财既有余,乃叹曰:“是岂所谓福哉!不已,且愚吾子孙。”因求族姻之穷者,悉为嫁娶振业之。乡人有急者,时亦周焉。比其没,家无一年之储。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终于乡里,享年四十八。轼登朝,追封武阳县君。呜呼,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,智能足以齐其家,斯已贤矣;况如夫人,能开发辅导成就其夫、子,使皆以文学显重于天下,非识虑高绝,能如是乎?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,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,今于夫人益见古人之可信也。
-
[宋代] 司马光
有德者皆由俭来也,俭则寡欲,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,可以直道而行;小人寡欲而能谨身节用,远罪丰家。故曰:俭,德之共。侈则多欲,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,枉道速祸;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,败家丧身,是以居官必贿,居乡必盗。故曰:侈,恶之大也。
为人父祖者,莫不思利其后世,然果能利之者鲜矣。何以言之?今之为后世谋者,不过广营生计以遣之,田畴连阡陌,邸肆跨坊曲,粟麦盈囷仓,金帛充箧笥,慊慊然求之尤未足,施施然自以为子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。然不知以义方训其子,以礼法齐其家,自于十数年中,勤身苦体以聚之,而子孙以岁时之间,奢蘼游荡以散之,反笑其祖考之愚,不知自娱,又怨其吝啬无恩于我而厉之也。
夫生生之资,固人所不能无,然勿求多余,多余希不为累矣。使其子孙果贤耶,岂疏粝布褐不能自营,死于道路乎?其不贤也。虽积金满堂室,又奚益哉?故多藏以遗子孙者,吾见其愚之甚。然则圣贤不预子孙之匮乏耶?何为其然也,昔者圣贤遗子孙以廉以俭。
-
[宋代] 司马光
吾本寒家,世以清白相承。吾性不喜华靡,自为乳儿,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,辄羞赧弃去之。二十忝科名,闻喜宴独不戴花。同年曰:「君赐不可违也。」乃簪一花。平生衣取蔽寒,食取充腹;亦不敢服垢弊以矫俗干名,但顺吾性而已。众人皆以奢靡为荣,吾心独以俭素为美。人皆嗤吾固陋,吾不以为病。应之曰:「孔子称『与其不逊也宁固』又曰『以约失之者鲜矣。』又曰『士志于道,而耻恶衣恶食者,未足与议也。』古人以俭为美德,今人乃以俭相诟病。嘻,异哉!」
近岁风俗尤为侈靡,走卒类士服,农夫蹑丝履。吾记天圣中,先公为群牧判官,客至未尝不置酒,或三行、五行,多不过七行。酒酤于市,果止于梨、栗、枣、柿之类;肴止于脯、醢、菜羹,器用瓷、漆。当时士大夫家皆然,人不相非也。会数而礼勤,物薄而情厚。近日士大夫家,酒非内法,果、肴非远方珍异,食非多品,器皿非满案,不敢会宾友,常量月营聚,然后敢发书。苟或不然,人争非之,以为鄙吝。故不随俗靡者,盖鲜矣。嗟乎!风俗颓弊如是,居位者虽不能禁,忍助之乎!
又闻昔李文靖公为相,治居第于封丘门内,厅事前仅容旋马,或言其太隘。公笑曰:「居第当传子孙,此为宰相厅事诚隘,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。」参政鲁公为谏官,真宗遣使急召之,得于酒家,既入,问其所来,以实对。上曰:「卿为清望官,奈何饮于酒肆?」对曰:「臣家贫,客至无器皿、肴、果,故就酒家觞之。」上以无隐,益重之。张文节为相,自奉养如为河阳掌书记时,所亲或规之曰:「公今受俸不少,而自奉若此。公虽自信清约,外人颇有公孙布被之讥。公宜少从众。」公叹曰:「吾今日之俸,虽举家锦衣玉食,何患不能?顾人之常情,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。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?身岂能常存?一旦异于今日,家人习奢已久,不能顿俭,必致失所。岂若吾居位、去位、身存、身亡,常如一日乎?」呜呼!大贤之深谋远虑,岂庸人所及哉!
御孙曰:「俭,德之共(hóng)也;侈,恶之大也。」共,同也;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。夫俭则寡欲,君子寡欲,则不役于物,可以直道而行;小人寡欲,则能谨身节用,远罪丰家。故曰:「俭,德之共也。」侈则多欲。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,枉道速祸;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,败家丧身;是以居官必贿,居乡必盗。故曰:「侈,恶之大也。」
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,孟僖子知其后必有达人。季文子相三君,妾不衣帛,马不食粟,君子以为忠。管仲镂簋朱纮,山节藻棁,孔子鄙其小器。公叔文子享卫灵公,史鰌知其及祸;及戌,果以富得罪出亡。何曾日食万钱,至孙以骄溢倾家。石崇以奢靡夸人,卒以此死东市。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,然以功业大,人莫之非,子孙习其家风,今多穷困。其余以俭立名,以侈自败者多矣,不可遍数,聊举数人以训汝。汝非徒身当服行,当以训汝子孙,使知前辈之风俗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