寒冷的岁末,百虫非死即藏,那蝼蛄彻夜呜叫而悲声不断。
冷风皆已吹得凛厉刺人,遥想那游子居旅外地而无寒衣。
结婚定情后不久,良人便经商求仕远离家乡。
独宿而长夜漫漫,梦想见到亲爱的容颜。
梦中的夫君还是殷殷眷恋著往日的欢爱,梦中见到他依稀还是初来迎娶的样子。
但愿此后长远过著欢乐的日子,生生世世携手共渡此生。
好梦不长,良人归来既没有停留多久,更未在深闺中同自己亲亲一番,一刹那便失其所在。
只恨自己没有鸷鸟一样的双翼,因此不能淩风飞去,飞到良人的身边。
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中,只有伸长著颈子远望寄意,聊以自遗。
只有依门而倚立,内心感伤,不禁的垂泪而流满双颊了。
此诗凡二十句,支、微韵通押,一韵到底。诗分五节,每节四句,层次分明。
惟诗中最大问题在于:一、「游子」与「良人」是一是二?二、诗中抒情主人公即「同袍与我违」的「我」,究竟是男是女?三、这是否一首怨诗?答曰:一、上文的「游子」即下文之「良人」,古今论者殆无异辞,自是一而非二。二、从全诗口吻看,抒情主人公显为闺中思好,是女性无疑。但第三个问题却有待斟酌。盖从「游子无寒衣」句看,主人公对「游子」是同情的;然而下文对良人又似怨其久久不归之意,则难以解释。于是吴淇在《选诗定论》中说:「前四句俱叙时,『凛凛』句直叙,『蝼蛄』句物,『凉风』句景,『游子』句事,总以叙时,勿认『游子』句作实赋也。」其间盖认定良人不归为负心,主人公之思极而梦是怨情,所以只能把「游子」句看成虚笔。其实这是说不通的。盖关四句实际上完全是写实,一无虚笔;即以下文对「良人」的态度而论,与其说是「怨」,宁说因「思」极而成「梦」,更多的是「感伤」之情。当然,怨与伤相去不过一间,伤极亦即成怨。但鄙意汉代文人诗已接受「诗都」熏陶,此诗尤得温柔敦厚之旨,故以为诗意虽忧伤之至而终不及于怨。这在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确是出类拔萃之作。一篇第一层的四句确从时序写起。岁既云暮,百虫非死即藏,故蝼蛄夜鸣而悲。「厉」,猛也。凉风已厉,以己度人,则游子无御寒之衣,彼将如何度岁!夫凉风这厉,蝼蛄之鸣,皆眼前所闻见之景,而言「率」者,率,皆也,到处皆然也。这儿天冷了,远在他乡的游子也该感到要过冬了,这是由此及彼。然后第二节乃从游子联想到初婚之时,则由今及昔也。「锦衾」二句,前人多从男子负心方面去理解。说得最明白的还是那个吴淇。他说:「言洛浦二女与交甫,素昧平生者也,尚有锦衾之遗;何与我同袍者,反遗我而去也?」「锦衾」句只是活用洛水宓妃典故,指男女定情结婚;「同袍」出于《诗经·秦风·无衣》,原指同僚,旧说亦指夫妇。窃谓此二句不过说结婚定情后不久,良人便离家远去。这是「思」的起因。至于良人何以远别,诗中虽未明言,但从「游子寒无衣」一句已可略窥端倪。在东汉末叶,不是求仕便是经商,乃一般游子之所以离乡北井之主因。可见良人之弃家远游亦自有其苦衷。朱筠《古诗十九首》云:「至于同袍违我,累夜过宿,谁之过欤?」意谓这并非良人本意,他也不愿离家远行,所云极是。惟游子之远行并非诗人所要表白的风客,读者亦无须多伤脑筋去主观臆测。
自「独宿」以下乃入相思本题。张庚《古诗十九首》云:「『独宿』已难堪矣,况『累长夜』乎?于是情念极而凭诸『梦想』以『见』其『容辉』。『梦』字下粘一『想』字,极致其深情也,又含下恍惚无聊一段光景。」正惟自己「独宿」而累经长夜,以见相别之久而相爱之深也(她一心惦记着他在外「寒无衣」,就是爱之深切的表现。),故寄希望于「梦想见容辉」矣。这一句只是写主人公的主观愿望,到下一节才正式写梦境。后来范仲淹写《苏幕遮》词有云:「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。」虽从游子一边着笔实从此诗生发演绎而出。
第三节专写梦境。「惟」,思也;「古」,故也。故欢,旧日欢好。梦中的丈夫也还是殷殷眷恋着往日的欢爱,她在梦中见到他依稀仍是初来迎娶的样子。《礼记·婚义》:「降,出御归车,而婿授绥,御轮三周。」又《郊特性》:「婿亲御授绥,亲之也。」「绥」是挽以登车的索子,「惠前绥」,指男子迎娶时把车绥亲处递到女子手里。「愿得」两句有点倒装的意思,「长巧笑」者,女为悦己者容的另一说法,意谓被丈夫迎娶携手同车而归,但愿此后长远过着快乐的日子,而这种快乐的日子乃是以女方取悦于良人赢得的。这是梦中景,却有现实生活为基础,盖新婚的经历对青年男女来说,长存于记忆中者总是十分美好的。可惜时至今日,已成为使人流连的梦境了。
第四节语气接得突兀,有急转直下的味道,而所写却是主人公乍从梦境中醒来那种恍恍惚惚的感受,半嗔半诧,似寤不迷。意思说好梦不长,良人归来既没有停留多久(「不须臾」者,犹现代汉语之「没有多久」、「不一会儿」),更未在深闺中(所谓「重闱」)同自己亲昵一番,一刹那便失其所在。这时才憬然惊察,原是一梦,于是以无可奈何的语气慨叹首:「只恨自己没有晨风一样的双翼,因此不能凌风飞去,追寻良人的踪迹。」「晨风」,鸟名,鹯属,飞得最为迅疾,最初见于《毛诗》,而《十九首》亦屡见。这是百无聊赖之辞,殆从《诗·邶风·柏舟》「静言思之,不能奋飞」语意化出,妙在近于说梦话,实为神来之笔,而不得以通常之比兴语视之也。
前人对最末一节的前两句略有争议。据胡克家《文选考异》云:「六臣本校云:『善(指李善注本)无此二句。』此或尤本校添。但依文义,恐不当有。」这两句不惟应当有,而且有承上启下之妙用,正自缺少不得。「适意」亦有二解,一种是适己之意。如陈祚明《采菽堂古诗选》云;「眄睐以适意,犹言远望可以当归,无聊之极思也。」另一种是指适良人之意,如五臣吕延济及吴淇《选诗定论》之说大抵旨谓后者。应解作适良人之意较好。此承上文「长巧笑」意,指梦中初见良俚的顾盼眼神,亦属总结上文之语。盖梦中既见良人,当然从眼波中流露了无限情思,希望使良人欢悦适意;不料稍留即逝,梦醒人杳,在自己神智渐渐恢复之后,只好「引领遥相睎」,大有「落月满屋梁,犹疑照颜色」(杜甫《梦李白》)的意思,写女子之由思极而梦,由暂梦而骤醒,不惟神情可掬,抑且层次分明。最终乃点出结局,只有「徙倚怀感伤,垂涕沾双扉」了,而全诗至此亦摇曳而止,情韵不匮。这后四句实际是从眼神作文章,始而「眄睐」,继而「遥睎」,终于「垂涕」,短短四句,主人公感情的变化便跃然纸上,却又写得那么质朴自然,毫无矫饰。《十九首》之神理全在此等处,真令读者掩卷后犹存遐思也。
从来写情之作总离不开做梦。《诗》、《骚》无论矣,自汉魏晋唐以迄宋元明清,自诗词而小说戏曲,不知出现多少佳作。甚至连程砚秋的个人本戏《春闺梦》中的关目与表演,都可能受此诗的影响与启发。江河万里,源可滥觞,信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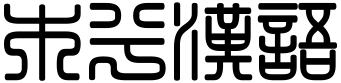
此诗为《古诗十九首》的第十六首,最早见于《文选》,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《古诗》中选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