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个大人先生,他把天地开辟以来的漫长时间看做是一朝,他把一万年当做一眨眼工夫,他把天上的日月当做是自己屋子的门窗,他把辽阔的远方当做是自己的庭院。他放旷不羁,以天为帐幕,以大地为卧席,他自由自在。停歇时,他便捧着巵子,端着酒杯;走动时,他也提着酒壶,他只以喝酒为要事,又怎肯理会酒以外的事!
有尊贵的王孙公子和大带的隐士,他俩听到我这样之后,便议论起我来。两个人揎起袖子,撩起衣襟要动手,瞪大两眼,齩牙切齿,陈说着世俗礼法,陈说是非,讲个没完。当他们讲得正起劲时,大人先生却捧起了酒器,把杯中美酒倾入口中,悠闲地摆动胡子,大为不敬地伸着两脚坐地上,他枕着酒母,垫着酒糟,不思不想,陶陶然进入快乐乡。他无知无觉地大醉,很久才醒酒,静心听时,他听不到雷霆的巨声;用心看时,他连泰山那么大也不看清;寒暑冷热的变化,他感觉不到;利害欲望这些俗情,也不能让他动心。他俯下身子看世间万事万物,见它们像江汉上的浮萍一般乱七八糟,不值得一顾;公子处士在他身边,他认为自己与他们更像蜾蠃和螟蛉一样。
酒德:饮酒的德性。
颂:文体的一种。
大人:古时用以指称圣人或有道德的人。
先生:对有德业者的尊称。大人先生,此处作者用以自代。
朝(zhāo):平旦至食时为朝。
万期(jī):万年。
期:周年。
扃牖(jiōngyǒu):门窗。扃,门;牖,窗。
八荒:四方与八隅合称八方,八方极远的地方为八荒。
幕、席:都是意动用法,以……为幕,以……为席。
如:往。
巵(zhī):古时一种圆形盛酒器。
觚(gū):古时一种饮酒器,长身,细腰,阔底,大口。
挈(qiè):提。
榼(kē):古时一种盛酒器。
务:勉力从事。
贵介:尊贵。
搢(jìn)绅:插芴于带间。搢,插;绅,大带。古时仕宦者垂绅插芴,故称士大夫为搢绅。搢一作为缙。
处士: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。
风声:名声。
所以:所为之得失。
奋袂(mèi)攘(rǎng)襟:挥动衣袖,捋起衣襟,形容激动的神态。奋,猛然用力;袂,衣袖;攘,揎,捋;襟,衣的交领,后指衣的前幅。
切齿:齩牙。
锋起:齐起,谓来势凶猛。锋一作为蜂。
于是:在这时。
甖(yīng):大肚小口的陶制容器。甖一作为罂。
槽:酿酒或注酒器。
漱醪(láo):口中含着浊酒。漱,含着;醪,浊酒。
髯:颊毛。
奋髯:撩起胡子。
箕踞(jījù):伸两足,手据膝,若箕状。箕踞为对人不敬的坐姿。
枕麴(qū)藉(jiè)糟:枕着酒麴,垫着酒糟。麴,酒母;藉,草垫。
陶陶:和乐貌。
兀然:无知觉的样子。
豁尔:此处指酒醒时深邃、空虚的样子。
切:接触。
感情:感于情,因所感而情动。
扰扰焉:纷乱的样子。
二豪:指公子与处士。
蜾蠃:青黑色细腰蜂。
螟蛉:蛾的幼虫。蜾赢捕捉螟蛉,存在窝里,留作它幼虫的食物,然后产卵并封闭洞口。古人误认为蜾赢养螟蛉为己子,螟蛉即变为蜾赢。此处以二虫比处士与公子。
这篇诗文可分为三层,起首至「惟酒是务,焉知其馀」为第一层。作者以如椽之笔,勾勒了一位顶天立地、超时超空的「大人先生」形象。他,「以天地为一朝,万期为须臾」,缩长为短,缩久远为一瞬,比庄子笔下的「以久特闻」的彭祖和「以八千岁为春,八千岁为秋」的大椿,越出几万倍。作者展开想像的翅膀,站在宇宙、天体的高度,俯视地球、人世的变幻,自然感觉渺小微末,那何必斤斤于一旦之交,汲汲于一夕之化。他,以「日月为扃牖,八荒为庭衢」,缩大为小,缩旷远为门庭,其胸怀之广阔,其眼界之高远,超尘拔俗,连庄子笔下的「绝云气,负青天」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」之大鹏,亦不能望其项背。以上四句,既突出「大人先生」之高大无比,横空出世,又为后文展示其「德」铺设一幅特大的背景。接着叙写「大人先生」的衣食住行,茕茕独立,不同凡响:「行无辙迹,居无室庐,幕天席地,纵意所如」,既然日月、八方只像扃牖、庭衢那么可以自由出入,普通车马何能载乘,普通室庐何能盖蔽,他——大人先生,豪放、脱羁,天当幕被,地当茵席,纵意所如,随心所欲,这可以说已达到庄子所论说、描叙的「逍遥游」境界了。至此,作者的笔触由虚而实,由前四句的空灵,到此四句的概述,再具体延伸到大人先生的「动止」,从而引出「酒」字,切入正题。他已不是一般的痛饮,而是狂饮。无论是静止时分还是行动时刻,不是「操巵执觚」,就是「挈榼提壶」,始终与酒为徒,「惟酒是务」。史载刘伶出门挂酒榼于车,令人荷锄随之,曰「死便掘地埋我」。这可以作为上面几句话的注脚。可见这个「大人先生」既是刘伶所向往的傲然世俗、卓然迥立之理想人物,也蕴含着刘伶本人的性格和影子。而「惟酒是务,焉知其馀」,看似超然物上,不屑与营营碌碌、争名夺利之世人为伍,但是举杯浇愁愁更愁,这里面却也或多或少发泄了不满现实的牢骚,包藏着嫉世愤俗的情愫。
第二层从「贵介公子」到「是非蜂起」,提出「大人先生」之对立面对其狂饮所作出的反响。围绕「酒」字,展开了饮与反饮的矛盾冲突,使文章波折起伏,激荡回转。「贵介公子」是既得利益者,无疑要维系其富贵利禄的名教礼法;而插笏系绅的官宦,作者称其为隐居的「处士」,这里不无讽刺之意,他们自然也要捍卫其赖以进阶的礼教法规。这些人不能容忍有近似疯狂的酒徒在一旁破坏、藐视礼俗大法。因而,「闻吾风声,议其所以」,一「闻」即「议」,显示了这些人狭隘的心胸和饶舌的伎俩;「议」之不过瘾,乃至于「奋袂攘襟,怒目切齿」,作者连下「奋」、「攘」、「怒」、「切」四个动词,活画出这批入围而攻之、气势汹汹的狰狞面貌。他们「陈说」的核心,自然是「礼法」,一时间,唾沫横飞,「是非」之说,蜂拥而起。根本没有直率之人的立足之地,没有耿介之士的容身之处。以上的描述,绝不是作者的随意想像,而是对当时黑暗腐败政治的一种概括和反映,真切而动人。
第三层,写「大人先生」对公子、处士攻击的回答。如果据理力驳,对这批沉湎礼法之徒,无可理喻,反而有损「大人先生」之旷达本性,倒不如反其道而行之,以率真的行为来冲破他们的名教礼法,大人先生于是索性变本加厉,不是一杯接着一杯、文文雅雅地喝,而是「捧罂承槽,衔杯漱醪」,多么的粗鲁狷狂,简直是满口满脸、满头满身都浸淫于酒了。不仅如此,饮酒的姿态也随之而变,坐则「奋髯箕踞」,越礼犯分;卧则「枕曲藉糟」,无法无天。大人先生心安理得,「无思无虑,其乐陶陶,兀然而醉」。这一系列倨傲不恭的行为,无疑是对那所谓的礼教的最大挑战,也是对「公子」、「处士」的最大棒喝。别看这些正人君子似乎春风得意,日日奔走于利禄,汲汲钻营于宦途,但神伤虑竭,尔虞吾诈,哪有先生那么陶然自乐。笔触至此,已切入「德」字。接下去,作者借醉态进一步扩展、申发「酒德」。醉是醉得那么「兀然」,毫无知觉;醒是醒得那么「恍尔」,心朗胸清。这里虽醉犹有三分醒,已醒还带三分醉。他的感官因此异于常人:听觉是「静听不闻雷霆之声」;视觉是「熟视无睹泰山之形」;触觉是「不觉寒暑之切肌,利欲之感情」。写听觉、视觉只是描绘醉态,是一种陪衬,目的是烘托出大人先生不为利欲撼情,甘居淡泊的高尚品德。《评注昭明文选》说:「酒中忘思虑,绝是非,不知寒暑利欲,此便是德。」评得非常确切。作者笔下的「大人先生」于已是「不闻」「不睹」「不觉」,而对人却看得异常透彻:「俯视万物,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」,世上万物是那么地乱七八糟漂泊无定,有什么可留恋一顾的。尔等公子、处士犹如蜾赢、螟蛉这样渺小的东西,何能长久。既称公子、处士为「二豪」,却又比喻为虫子,是极妙的讽刺,极度的蔑视。这一层的词意似乎多为自我解嘲,不辨是非,而通观全文,却是嘻笑怒骂,痛快淋漓,泾渭分明,是非自辨。那位「大人先生」虽沉湎于酒,却不沉湎其心,酒德由是而兴;而那公子、处士虽不沉湎于酒,却沉湎于札法,满口的说教越显示出他们的无德。所谓的「有德者」最无德,所谓的「无德者」最有德,正是这篇文章的题旨所在。
这篇骈文全篇以一个虚拟的「大人先生」为主体,借饮酒表明了一种随心所欲,纵意所如的生活态度,并对封建礼法和士大夫们作了辛辣的讽刺。语言形象生动,清逸超拔,音韵铿锵,主客对峙,铺叙有致,文气浩荡,笔酣墨饱,有飘然出尘,凌云傲世之感。作者把那些「贵介公子」,「缙绅处士」们的丑态和「大人先生」「无思无虑,其乐陶陶」的悠然自在相对比,达到了鲜明的讽刺效果。作者极力渲染了酒醉后的怡然陶醉之感,视缙绅公子们如虫豕一般,于不动声色之中作了尽情的嘲讽。
明·金圣叹《天下才子必读书》:从来只说伯伦沉醉,又岂知其得意在醒时耶?看其「天地一朝」等,乃是未饮以前,「静听不闻」,乃是既醒以后,则信乎众人皆醉,伯伦独醒耳。
清·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:撮庄生之旨,为有韵之文,仍不失潇洒自得之趣,真逸才也。
清·李扶九《古文笔法百篇》:……是颂绝不假饰一字,虽不可训,然七贤中较之钱癖则远过之矣。本是解嘲文,乃大其题目日「颂」。颂中议论大方,词气雄豪,亦与题称,仍有波折章法,晋文中之杰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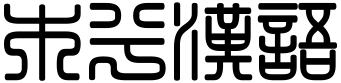
《酒德颂》是魏晋诗人刘伶创作的一篇骈文。这篇文章虚构了两组对立的人物形象,一是「唯酒是务」的大人形象,一是贵介公子和缙绅处士,他们代表了两种处世态度。大人先生纵情任性,沉醉于酒中,睥睨万物,不受羁绊;而贵介公子和缙绅处士则拘泥礼教,死守礼法,不敢越雷池半步。此文以颂酒为名,表达了作者刘伶超脱世俗、蔑视礼法的鲜明态度。文章行文轻灵,笔意恣肆,刻画生动,语言幽默,不见雕琢之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