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时,毗耶离大城中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,名叫维摩诘,他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,培植了深厚坚固的善根,获得了洞见诸法不生不灭的智慧,达到了无生法忍的菩萨境界;他辩才无碍,以种种神通游戏三界,济度天人;他掌握了一切修持法门,获得了佛菩萨才具有的四无所畏;他能够降伏魔怨惑障,深谙佛法玄奥的真谛;他善于用般若智慧度化众生,又通达教化众生的种种方便法门;于是,他圆满成就了度化众生的大悲宏愿,明了众生的心意趣向,又能善于分别众生的根机利钝。他很早以来就深入佛道,心智已极灵明纯净,坚定不移地尊奉大乘佛法,弘扬大乘精神;他的任何言行都十分严谨,经过缜密而细致的思考;他的任何举止都具备佛的庄严威仪,心智宽广如海;他受到诸佛如来的嘉美、赞叹和颂扬,也深受佛陀弟子、帝释、梵天及世间君王的崇敬。为了济度世人,维摩诘运用善巧方便法门,以居士身份居住在毗耶离城中。
维摩诘拥有无量的财富,经常周济贫穷无助的众生;他本人戒行清净,堪为典范,借此示教于那些毁坏禁戒之人;他以极深的忍辱修为,摄化、调伏瞋恚成性的众生;他勇猛精进,勤于修行,借此以警策、摄化懈怠懒散的众生;他具有极深的禅定功夫,一心不乱,借此以摄化心浮意躁、胡思乱想的烦恼众生;他以坚定的无上智慧,摄化愚痴无智、妄见邪智的众生。
维摩诘虽然身为白衣居士,却严谨持守出家沙门的清净戒律;他虽然居住在世俗社会的家庭中,却完全不执着于欲界、色界和无色界的尘俗世事;他虽然有妻子儿女,却恒常修习清净梵行;他虽然也有六亲眷属,却恒常享受着超越眷属羁绊的快乐;他虽然身着珍贵华美的服饰,却更以功德道行成就的吉瑞相好来庄严其身;他虽然也像常人一样饮水吃饭,却更以禅定的喜悦为滋味;如果他来到赌博、游戏的场所,都是为了度化沉迷其中的世人;他虽然也接受外道异端的学说,却从来不会影响其对佛法的纯正信仰;他虽然通晓世俗的学问典籍,却恒常爱好佛法。正因为这样,维摩诘深受一切众生的崇敬和爱戴,在接受供养者中居于首位。
维摩诘以长者的身份执持正法,处理世俗事务,摄护毗耶离城的男女老幼;他虽然像世俗之人那样从事一切谋生事业,且常常获得十分可观的利润,却从来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;他经常游走于一切街头闹市,那是为了教化、饶益众生;他参与管理国家的世俗政务,那是为了救护一切众生;每当他到了公开讲论的地方,总以大乘法教化众生;每当他到了学校讲堂,总以真知正见开导学童;他甚至进入各种青楼妓院,那是为了显示淫欲的罪过;他也走进各种闹市酒馆,那是为了教化那些醉生梦死之徒,使他们确立正念、正智和正志。
维摩诘如果出现在长者之中,他受到长者们的尊敬,为他们宣说殊胜的佛法;如果出现在居士之中,他受到居士们的尊敬,能劝导他们断除贪欲和执着;如果出现在刹帝利之中,他受到刹帝利的尊敬,教导他们培养忍辱精神和亲和力;如果出现在婆罗门之中,他受到婆罗门的尊敬,教导他们破除自大和傲慢;如果出现在大臣之中,他受到大臣们的尊敬,教导他们奉守正法,依法辅政;如果出现在王子之中,他受到王子们的尊敬,教导他们忠孝的道理;如果出现在内官之中,他受到内官们的尊敬,教化宫女,使她们正直忠贞,遵守法律和伦理;如果出现在平民百姓之中,他受到平民百姓的尊敬,教导他们行善积德,培植福徳善根;如果出现在诸梵天之中,他受到诸梵天的尊敬,为他们开示殊胜无比的佛法智慧;如果出现在帝释天之中,他受到帝释天的尊敬,为他们示现三界无常、缘起性空的佛法义理;如果出现在护法诸天王之中,他受到护法诸天王的尊敬,教导他们护持佛法及一切众生。
长者维摩诘,就是以如此种种无量善巧方便智慧,来饶益众生。现在,维摩诘又运用善巧方便法门,示现身患疾病。由于维摩诘身体患病的缘故,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、婆罗门,以及诸位王子、百官臣僚等等,数以千计的人士都前去探视他的疾病。对于这些众多前来探视的众人,维摩诘就以自己身体患病为缘由,向他们广说大乘不可思议法门:
“诸位仁者大德啊,我们这血肉之身是由‘四大’、‘五蕴’和合而成,本无自性,是变化无常的,不够强壮,没有力量,也不坚固,只是转瞬就会朽坏的东西,不可相信依赖啊;这血肉之躯是诸苦、烦恼、各种疾病之渊薮。诸位仁者大德啊,这样的血肉之身,一切明智之士都不会去贪恋依赖的。
“这身体如同水面上聚集的浮沫,不可拈取搓摩;这身体如同水面上漂浮的气泡,不能长久存在;这身体如同阳光炙烤下产生的蜃影,是从烦恼和贪欲中产生;这身体如同芭蕉杆,中间空空,没有坚固的实体;这身体如同幻影,是由于无明颠倒而产生的妄想;这身体如同梦中镜象,是分别意识的虚无妄见;这身体如同影像,是过去所造之业因缘而起的显现;这身体如同空中回荡的声响,是各种因缘和合的产物;这身体如同天空浮云,瞬间即随风飘逝;这身体如同闪电,刹那不住;这身体没有恒常不变的主宰,就像大地没有永恒的主宰一样;这身体没有恒常不变的自性,就像燃烧的火一样;这身体没有长久的寿命,就像短暂的飘风一样;这身体并非人我,没有定体,就像水无定形一样;这身体并不真实,是地、水、风、火‘四大’临时寄居之所;这身体犹如虚空,既不是一个真我,也不是属于真我所有;这身体没有知觉灵性,就像草木瓦砾一样;这身体没有自主性的行为,只是随业力之风牵引而轮转生死;这身体污秽不净,充满污秽恶臭;这身体虚假不实,尽管每天都给它沐浴穿衣饮食加以保养,但它最终必定归于磨灭;这身体是诸多灾祸的汇集处,时刻受到众多病痛的苦恼;这身体如同丘之将颓、井之将枯,受到衰老朽坏的逼迫;这身体毫无定性,终归有一天要走向死亡;这身体如同毒蛇,如同怨贼,如同空荡荡的聚落,是由‘五蕴’、 ‘十八界’、 ‘十二入’共同组合而成的。
“诸位仁者大德啊,这血肉之身实在是灾患,确实应该厌离,应该欣乐于追求佛身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所谓佛身,就是法身啊。此法身是从无量功德智慧中产生的,是从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知见中产生的,是从慈、悲、喜、舍‘四无量心’中产生的,是从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柔和、勤行、精进、禅定、解脱、三昧、多闻、智慧等修行方法中产生的,是从种种方便法门中产生的,是从‘天眼通、天耳通、神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漏尽通’六神通中产生的,是从‘宿命明、天眼明、漏尽明’三明中产生的,是从‘三十七道品’中产生的,是从止观中产生的,是从‘十力’、‘四无所畏’、‘十八不共法’中产生的,是从断一切不善法、集一切善法中产生的,是从真如实际中产生的,是从精进修持而不放逸中产生的,如来法身是从这一切无量清净法中产生的。诸位仁者大德,如果你们想要修得佛身,断除一切众生的病患苦恼,就应该发起无上正等正觉之心。”
就是这样,维摩诘为所有前去探视他病情的众生,如此这般演说佛法,令数以千计的探视者都发起无上正等正觉之心。
游戏神通:指能随意自在运用神通,济度众生。“神通”指一种超自然的、不可思议的功能和力量。佛、菩萨、阿罗汉具有六神通:天眼通、天耳通、神足通、天耳通、宿命通、漏尽通。这里指维摩诘能任意运用种种神通在世间随缘度众。
大乘:相对于声闻、缘觉等小乘的菩萨乘、佛乘,其特点是不以自度为终的,而把慈悲普度、成就佛道作为最终目标。大乘与小乘主要有以下区别:第一、佛陀观不同。有些小乘部派(主要是上座部)认为,释迦牟尼是一位依靠自己的修行而觉悟的人,是历史上的教主,是唯一的佛;另外一些部派(如大众部)则相对神化了佛陀。大乘则完全把佛陀神格化,看作崇拜的偶像,提出了二身、三身,甚至十身的说法,并且认为三世十方还有无数佛。第二、修行目标不同。部派佛教修行的最高目标是成就阿罗汉果和辟支佛果,即指灭尽烦恼、超越生死、自我的解脱;大乘佛教认为这一目标不够高,修行的最高目标应该是成佛,建立佛国净土,至少做个“上求菩提,下化众生”的菩萨,即佛的候补者。第三、修行方法不同。小乘一般修三学(戒、定、慧)、八正道、四谛、十二因缘;大乘则兼修六度(六种度众生的方法,即持戒、禅定、智慧、精进、布施、忍辱)和四摄(布施、爱语、利行、同事)的菩萨行。大乘佛教强调以菩提为目标,提倡“普度众生”,因此大乘特别重视居士佛教,“小乘认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,非出家过禁欲生活不可;而大乘,特别在其初期,则以居家的信徒为主。并且有些事只有在家才具备条件去做,例如布施中的财施,出家人不许集财,就不能实行。因此,大乘一开始,很重视在家,不提倡出家”(吕激《印度佛学源流略讲》),“大乘佛教的发展始终把在家居士的菩萨行视为关键因素,甚至有学者认为,小乘佛教是以僧侣为中心展开的,而大乘佛教则是从在家信徒中兴起的”(潘桂明《印度大乘佛教》)。池田大作也认为:“小乘佛教徒埋头于只有专门的出家僧侣才能理解的教义研究,把佛教当作一种封闭的宗教。而大乘教徒却不承认出家与在家的差别,他们把佛教作为一般化的、广为开放的宗教。”(《我的佛教观》)居士佛教发端于原始佛教,但它真正成为一种潮流,则是在大乘佛教时期。第四、佛教理论。“在理论上,大乘主张我法俱空,一切皆空,小乘,特别是有部,局限于佛说的法都是实在的,是一种概念实在论。”(吕激《印度佛学源流略讲》)鸠摩罗什《大乘大义章》卷下说:“有二种论,一者大乘论,说二种空:众生空、法空;二者小乘论,说众生空。”小乘佛教一般主张“我空法有”,否认“人我”的实在性,承认外境外法的存在;大乘佛教主张“我法二空”,不仅否认“人我”,也否认“法我”。大、小二乘都主张“空”,大乘空得更彻底些。吉藏《三论玄义》卷上谓小乘(《成实论》)中亦有“二空”说,大、小二乘的理论差别集中在对“空”的理解上,略有四点:一、“小乘析法明空,大乘本性空寂”;二、“小乘但明三界内人、法二空”,“大乘明三界内外人、法并空”;三、“小乘但明于空,未说不空;大乘明空,亦辨不空”,所谓“空者,一切生死;不空者,谓大涅乐”;四“小乘名为但空,谓但住于空;菩萨名不可得空,空亦不可得也”。就是说,大乘佛教的唯心哲学更精致、更彻底。第五、佛法标准。小乘主张“三法印”,即“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架寂静”。大乘主张“一法印”,即“一实相印”。有学者为了打通大小二乘,主张“一法印”即“三法印”,“三法印”即“一法印”。
白衣:指在家世俗之人。古印度婆罗门和世俗之人多穿着白衣,故以“白衣”称之。出家沙门则穿缁衣或染衣,故沙门亦称为“缁衣”。
沙门:梵语音译,又作“桑门”、“丧门”,意译为“息心”、“净志”等,泛指出家修道之人。
梵行:“梵”为清净义,“梵行”即清净之行。
禅悦:禅定中感受到的愉悦。
世典:佛典之外的世俗典籍。
治生谐偶:经营谋生。治生,即谋生。谐偶,和合,指倍数,表示多的意思,引申为顺利。
四衢:城中四通八达的街道。衢,街道,大路。
刹利:全称“刹帝利”,为古印度四种姓之一,是印度古代之王族。古印度统治者用种姓制度规范社会各个等级的社会职责:第一种姓“婆罗门”,是执掌宗教事务的僧侣和祭司,垄断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大权,自诩为“人间之神”、“人中之神”;第二种姓“刹帝利”,是执掌军政大权的武士和军事贵族,是世俗王权的主要支柱;第三种姓“吠舍”,是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农民、手工业者和商人,是社会生产的主导力量;第四种姓“首陀罗”,是为以上三个种姓服务的奴隶,从事极其卑贱的工作。另有第五种姓“旃陀罗”,比首陀罗地位更加低贱,主要是狱卒、盗贼、屠夫、打猎、捕鱼之类的人。《摩登伽经》卷上云“旃陀罗者,造作恶业,凶暴残害;欺诳众生,无慈愍心;以是因缘,名为卑贱。”
婆罗门:古印度四种姓之一,位居四种姓之首,信奉婆罗门教。婆罗门编造婆罗门至上说,“婆罗门姓梵王口生,刹帝利姓梵天臂生,毗舍(吠舍)种姓梵天髀生,从于梵足乃生首陀罗(《金刚针论》)。
梵天:即色界之初禅天。此指梵天众生。
帝释:又作“释提桓因”、“释迦提桓因陀罗”,为欲界忉利天(即三十三天)之主神,居于须弥山顶的善见城。在古印度吠陀思想中,他被视为唯一的“大梵”。
无常:指一切诸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,都处在不断地生灭变化之中,没有恒常不变的自性或实体。
护世:指护世四天王。“四天王”为帝释的部属,居于须弥山半腰,分别护持一天下。东方为持国天王,南方为增长天王,西方为广目天王,北方为多闻天王。
不怙(hù):不去依恃。怙,意为依靠、依恃。
业缘:业感缘起、十二因缘,意为一切众生的生死流转,都是由众生的业因相感而缘生。善果为善业所缘起,恶果为恶业所缘起,业缘为善恶果报的因缘。业,梵语意译,音译为“羯磨”,为造作之义,泛指一切身心活动。佛教将“业”分为身、语意三类:身业,指身体的行为;语业,也称“口业”,指言语;意业,指思想活动。《大毗婆沙论》中说:“三业者,谓身业、语业和意业。问此三业云何建立?为自性故,为所依故,为等起故。若自性者,应唯一业,所谓语业,语即业故;若所依者,应一切业皆名身业,以三种业皆依身故;若等起者,应一切业皆名意业,以三皆是意等起故。”佛教认为,善业是招感乐果的因缘,恶业是招感苦果的因缘。对于业的善恶性质及其果报,《成实论》卷七中说:“业报三种,善、不善、无记;从善、不善生报,无记不生。”“无记”就是非善非恶,没有后果产生。
四大:古代印度哲学认为构成宇宙万物有四个最基本的因素,即地、水、风、火。人身由色、心二法构成,色法(色身)由“四大”构成。
我、我所:我,指自我、自身;我所,指我所有的事物,广指一切法。佛教认为,一切众生都是五蕴和合的产物,并不存在一个恒常不变的实体或主宰者,因而是“人无我”;同样,自身之外的一切诸法,也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产物,并不是恒常不变的实在,因而法也是“无我”;总之,无我我所,故应远离。
阴界诸入:指五阴、十八界、十二入。五阴,又作“五蕴”, 指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阴,荫覆之义;蕴,积聚、类别的意思。“色蕴”大致相当于物质现象,包括地、水、火、风“四大”和由“四大”所组成的“五根”(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种感觉器官)、“五境”(与五根相对应的五种感觉对象: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)以及所谓的“无表色”(指依身、口、意发动的善恶之业,生于身内的一种无形的色法)。“受蕴”即感受,指在外界作用下产生的各种感受。一般分为“苦”、“乐”、“舍”(不苦不乐)三种不同的感受。“想蕴”相当于知觉或表象。人们通过对外境的接触而执取颜色、形状等种种相状,并形成种种名言概念,即为“想蕴”。“行蕴”相当于意志和行动,泛指一切身心活动。“识蕴”指意识或认识作用,“识”为“了别”之义。佛教认为众生的身体都是此五蕴和合而成的。十八界,指具有认识功能的“六识”(能依之识)、发生认识功能的“六根”(所依之根)、作为认识对象的“六境”(所缘之境)。界,为种类、种族义。“六识”即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;“六根”即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;“六境”即色、声、香味、触、法。十二入,指“六根”(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)和“六境”(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)“十二法”。“六根”与“六境”彼此互入而生感受,故称“十二入”;“六根”和“六境”为产生心和心所之处,故又称“十二处”。
法身:又名“自性身”、“法性身”,即诸佛所证的真如法性之身,此法身以佛法成身或身具一切佛法,为佛法第一义谛,因而具有本体之意义。佛有“法、化、报”三身,此处法身应指报身。
三昧:梵语音译,又作“三摩地”、“三摩提”,意译为“定”、 “正定”,是一种将心定于一处的禅定境界。波罗蜜:梵语音译,意译为“度”、“到彼岸”,指把众生从生死此岸度到涅粲彼岸的方法或途径。
六通:六种神通,分别为天眼通、天耳通、神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漏尽通。
三明:即宿命明(明了自身及一切众生过去世种种生死因缘的智慧)、天眼明(明了自身及一切众生未来世种种生死因缘的智慧)、漏尽明(断尽一切烦恼的智慧)。
止观:“止”即禅定,止散乱心,专注一境;“观”即智慧,观察一切真理。“止观”就是定慧双修的意思,是佛教两种最基本的修行方法。僧肇《注维摩诘经》卷五:“系心于缘谓之止,分别深达谓之观。止观,助涅槃之要法。”
放逸:指放纵逸乐而不能勤修善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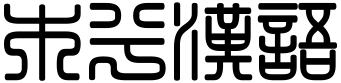
维摩诘所说经是佛教大乘经典。一称《不可思议解脱经》,又称《维摩诘经》《净名经》。后秦鸠摩罗什译有3卷,14品。叙述毗耶离(吠舍离)城居士维摩诘,十分富有,深通大乘佛法。通过他与文殊师利等人共论佛法,阐扬大乘般若性空的思想。其义旨为“弹偏斥小”“叹大褒圆”,批判一般佛弟子等所行和悟境的片面性,斥责歪曲佛道的绝对境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