顺德府通判厅记
余尝读白乐天《江州司马厅记》,言自武德以来,庶官以便宜制事,皆非其初设官之制。自五大都督府,至于上中下那司马之职尽去,惟员与体在。余以隆庆二年秋,自吴兴改倅邢州。明年夏五月茬任,实司那之马政。今马政无所为也,独承奉太仆寺上下文移而已。所谓司马之职尽去,真如乐天所云者。
而乐天又言:江州左匡庐,右江、湖,土高气清,富有佳境。守土臣不可观游,惟司马得从容山水间,以足为乐。而邢,古河内,在太行山麓。《禹贡》衡津、大陆,并其境内。太史公称”邯郸亦漳、河间一都会”,“其谣俗犹有赵之风”。余夙欲览观其山川之美,而日闭门不出,则乐天所得以养志忘名者,余亦无以有之。然独爱乐天襟怀夷旷,能自适,现其所为诗,绝不类古迁谪者,有无聊不平之意。则所言江州之佳境,亦偶寓焉耳!虽微江州,其有不自得者哉?
余自夏来,忽已秋中,颇能以书史自误。顾街内无精庐,治一土室,而户西向,寒风烈日,霖雨飞霜,无地可避。几榻亦不能具。月得俸黍米二石。余南人,不惯食黍米,然休休焉自谓识时知命,差不愧于乐天。因诵其语以为《厅记》。使乐天有知,亦以谓千载之下,乃有此同志者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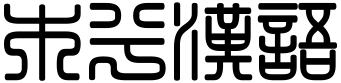
归有光六十二岁时,调任顺德通判,管马政。通判是副职,明升暗降,他为此感到愤慨,曾连上乞休文而被上司搁置。马政虽是闲职,他还是很认真地办了一些实事,并以旷达的心情写了两篇文章记述这一段生活。《顺德府通判厅记》是其中的一篇。
这篇文章的开头很巧妙,有如神来之笔引出唐代曾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,而且是读他的《江州司马厅记》。开头一段的文字是不动感情的,但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潜台词已经不说自明,第二段感情波澜起伏。白乐天谕居江州,犹有匡庐江湖之佳境可供养志忘名,可自己呢,亦失以有之,比白乐天的处境更差。但是,白居易虽然是个迁谪者却没有无聊不平之意,胸怀夷旷,能自适,是归有光所赞同的。因此,“虽微江州,其有不自得哉”一语,既是说白居易,也是说自己。关于在顺德的苦中自娱的情况,容容几笔就带过了。一则白居易写文于前,归有光写文于后,同是写被谪贬管马政,总得另闢蹊径;二则归有光撰写此文本意不在记叙在顺德的琐事,而在于抒发与白居易共鸣的情感。结尾处点睛之笔说得很明白:儒家的“乐夭知命”的思想,是白居易和归有光所共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