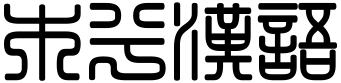公孙丑问道:“先生如果做了齐国的卿相,得以推行自己的主张,即使成就了霸王的事业,也是不奇怪的。如果这样,您会动心吗?”
孟子说:“不。我四十岁以后就不再动心了。”
公孙丑说:“这么说,先生远远超过孟贲了。”
孟子说:“这不难,告子在我之前就做到不动心了。”
公孙丑说:“做到不动心,有什么方法吗?”
孟子说:“有。北宫黝培养勇气的办法是,肌肤被刺也不颤动发抖,眼睛被戳也能目不转睛,但他觉得,受了他人一点小委屈,就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鞭打了一般。既不平民百姓的侮辱,也不受大国之君的侮辱。在他看来,刺杀大国之君,和刺杀普通老百姓是一样的。他不畏惧诸侯王。有人骂他,他一定回击。孟施舍培养勇气呢,是说:‘我把不能取胜的形势看成可以取胜。如果先估量敌人的力量才前进,考虑到可以取胜才交战,这是害怕敌人的三军。我孟施舍咋能战无不胜,只能无所畏惧罢了。’(培养勇气的方法,)孟施舍像曾子,北宫黝像子夏。这两个人的勇气,不知道谁更强,然而,孟施舍所守的较能符合要领。从前曾子对子襄说:‘你喜欢勇敢吗?我曾经从先生那里听过什么是大勇:自我反省而发现正义不在我,那么即使是普通百姓,我也不去恐吓他;自我反省而认为正义在我,即使面对千军万马,我也勇往直前。’孟施舍所守的是一身盛气,曾子却能有所反省,循理而动,所以,孟施舍又不如曾子所守把握住要领。”
孟子说:“告子讲过:‘言语有过失,不必到内心去寻求原因,心中有所不安,不必求助于意气。’心中有所不安,不必求助于意气,是可以的;言语有过失,不必到内心去寻求原因,却不可以。思想意志呢,是感情意气的统帅,感情意气是充满体内的力量。思想意志到哪里,感情意气就跟着到哪里。所以说:‘要坚定自己的思想意志,也不要滥用感情妄动意气。’”
公孙丑说:“既然说‘思想意志到哪里,感情意气就跟着到哪里’,又说‘要坚定自己的思想意志,也不要滥用感情妄动意气’,为什么呢?”
孟子说:“思想意志专一,就能调动感情意气跟随它;感情意气专一,就会影响思想意志。比方说跌倒、奔跑,这是下意识的气有所动,但也能反过来扰动心志。”
公孙丑说:“请问先生擅长哪方面?”
孟子说:“我能够判断人们的语言,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。”
公孙丑说:“请问什么叫做浩然之气?”
孟子说:“难以讲清楚啊。它作为一种气,是最强大,最刚健的,用正直来培养它而不伤害它,就能充塞于天地之间。它作为一种气,是合乎义和道的;没有这个,它就疲弱了。它是日积月累的正义所生长出来的,不是偶然地有过正义的举动就取得的。如果行为有愧于心,气就萎缩了。因此我说,告子不曾懂得义,因为他把义看做是外在的东西。(对浩然之气,)一定要培养它,不能停止下来;心里不能忘记它,也不妄自助长它。不要像那个宋国人一样。宋国有个担心禾苗长不快而把它拔高的人,非常疲倦地回去,告诉他的家人说:‘今天累坏了,我帮助禾苗长高了。’他的儿子跑过去看,禾苗都枯槁了。天底下不拔苗助长的人少见啊。(说到浩然之气,)以为培养无益而放弃的,是不为禾苗除草的人;有意帮助它生长的,是拔苗的人。不仅无益,而且有害。”
公孙丑说:“怎样才算‘能够判断人们的语言’?”
孟子说:“偏颇的言辞,知道它在哪一方面被遮蔽而不明事理;过分的言辞,知道它耽溺于什么而不能自拔;邪僻的言辞,知道它违背了什么道理而乖张不正;搪塞的言辞,知道它在哪里理屈而终于词穷。言辞的过失产生于思想认识,危害于政治;把它体现于政令措施,就会危害具体工作。如果圣人复生,一定会赞同我的话。”
公孙丑说:“宰我、子贡善于说话,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善于阐述德行。孔子兼而有之,但他又说:‘我对于辞令是不擅长的。’那么先生您已经是圣人了吧?”
孟子说:“呦!这是什么话呀?从前子贡问孔子道:‘先生是圣人了吧?’孔子说:‘圣人,我做不到,我只是学习而不知满足,教育而不知疲倦。’子贡说:‘学习而不知满足,是明智;教育而不知疲倦,是仁爱。明智而且仁爱,先生已经是圣人了!’圣人,连孔子都不愿自居,你说的是什么话呀!”
公孙丑说:“以前我听说:子夏、子游、子张都有某一方面得到孔子真传,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则全面地得到孔子真传但气象比孔子小些。请问您自居于哪一种人?
孟子说:“暂且不谈这个。”
公孙丑说:“伯夷、伊尹怎么样?”
孟子说:“与孔子不同。不是他理想的君主,他不服侍;不是他理想的百姓,他不使唤;天下太平就进取,天下大乱就退隐,这是伯夷。服侍不理想的君主有什么关系,使唤不理想的百姓有什么关系;天下太平也进取,天下大乱也进取,这是伊尹。可以做官就做官,可以不做就不做,可以长久留任就长久留任,可以迅速离任就迅速离任,这是孔子。这都是古代的圣人,我没有一样能做到;要说愿望的话,我愿学孔子。”
公孙丑说:“伯夷、伊尹和孔子不是一样的吗?”
孟子说:“不。自从有人类以来,还没有像孔子那样的。”
公孙丑说:“那么他们有相同之处吗?”
孟子说:“有。如果得到纵横百里的土地而做君王,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觐而统一天下。做一件不义的事,杀一个无辜的人因而得到天下,他们都不干。这是他们的相同之处。”
公孙丑说:“请问他们又有什么不同呢?”
孟子说:“宰我、子贡、有若的聪明足以了解孔子。他们的智慧再低下,也不至于偏袒他们所喜爱的人。宰我说:‘凭我对先生的观察,他比尧、舜强多了。’
子贡说:‘看某时某地的礼制,就可以了解它的政治状况;听某时某地的音乐,就可以了解它的道德风气。从百代以后,去评价百代以来的君王,没有人能违背这个规律而有所隐蔽。我认为自从有人类以来,还没有像先生那样的人。’有若说:‘难道只是人有高下之分吗?麒麟对于走兽,凤凰对于飞鸟,泰山对于土堆,河海对于积水,都算是同类。圣人对于人,也是同类。突出于所属的类,超拔于所属的群,自从有人类以来,还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。’”
加:任。
孟贲:古代勇士,卫国人。
告子:名不害,与孟子同时而年长于孟子,曾受教于墨子。
北宫黝(yǒu):姓北宫,名黝,战国时期齐国人。
桡(náo):同“挠”,退却。
褐(hè)宽博:指卑贱者。褐,粗布衣服;宽博,宽大的衣服。褐、宽博,都是贱者之服。
孟施舍:古代勇士。
会:指交战。
曾子:即曾参,孔子弟子。子夏:姓卜名商,孔子弟子。
子襄:曾子弟子。
缩:直。
暴:乱。
蹶(jué):跌倒。
浩然:形容盛大流行的样子。
义袭:义,偶然从外进入内心。袭,偷袭。
慊(qiàn):不满意,怨恨。
正:止,中止。
芒芒然:疲倦的样子。
病:疲倦。
耘:除草。
诐(bì):偏颇。蔽:遮蔽。淫:过分。陷:沉溺。
邪:邪僻,不正。离:背离。遁:逃避。
宰我:孔子弟子宰予。子贡:孔子弟子端木赐。
冉牛:孔子弟子冉耕,字伯牛。闵子:孔子弟子闵损,字子骞。颜回:孔子弟子颜渊。
子游:孔子弟子言偃。子张:孔子弟子颛孙师。
伊尹:商汤的贤臣。
何:同“可”。
班:同等,并列的意思。
有若:孔子的弟子。
污:夸大。阿(ē)徇私,偏袒。
等:指分出等次。
违:指违背“见其礼而知其政,闻其乐而知共德”的规律。
垤(dié):小土堆。行潦(lǎo):路上的积水。潦,雨水。
这段话很长,但核心意思是论“善养浩然之气”。在孟子看来,以“浩然之气”来当齐国的卿相,并非难事。他并不欣赏北宫黝、孟施舍的所谓“勇气”,也不欣赏告子关于意志、意气的见解,他只赞同孔子关于大勇的理论——关键是要正义在手,正气在胸。孟子暗中把自己比作孔子一类的圣人,他借孔门弟子之口,盛赞孔子,认为孔子是古往今来天下第一大圣人,是具有大勇的人,胸中有“浩然正气”。
孟子所阐释的浩然之气,对培养中华民族的民族正气和民族气节,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。文天祥在就义前所写的《正气歌》,就是秉承于孟子的这一教诲。
另外,文中提到“揠苗助长”的故事,是为了告诉人们,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,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,才能取得成功。
“告子谓于言有所不达,则当舍置其言,而不必反求其理于心;于心有所不安,则当力制其心,而不必更求其助于气,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动之速也。孟子既诵其言而断之曰,彼谓不得于心而勿求诸气者,急于本而缓其末,犹之可也;谓不得于言而不求诸心,则既失于外,而遂遗其内,其不可也必矣。然凡曰可者,亦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耳。若论其极,则志固心之所之,而为气之将帅;然气亦人之所以充满于身,而为志之卒徒者也。故志固为至极,而气即次之。人固当敬守其志,然亦不可不致养其气。盖其内外本末,交相培养。此则孟子之心所以未尝必其不动,而自然不动之大略也。”
“知言者,尽心知性,于凡天下之言,无不有以究极其理,而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。浩然,盛大流行之貌。气,即所谓体之充者。本自浩然,失养故馁,惟孟子为善养之以复其初也。盖惟知言,则有以明夫道义,而于天下之事无所疑;养气,则有以配夫道义,而于天下之事无所惧,此其所以当大任而不动心也。”
“言所行一有不合于义,而自反不直,则不足于心而其体有所不充矣。然则义岂在外哉?告子不知此理,乃曰仁内义外,而不复以义为事,则必不能集义以生浩然之气矣。”
“舍之不耘者,忘其所有事。揠而助之长者,正之不得,而妄有作为者也。然不耘则失养而已,揠则反以害之。无是二者,则气得其养而无所害矣。如告子不能集义,而欲强制其心,则必不能免于正助之病。其于所谓浩然者,盖不惟不善养,而又反害之矣。”
“人之有言,皆本于心。其心明乎正理而无蔽,然后其言平正通达而无病;苟为不然,则必有是四者之病矣。即其言之病,而知其心之失,又知其害于政事之决然而不可易者如此。非心通于道,而无疑于天下之理,其孰能之?彼告子者,不得于言而不肯求之于心;至为义外之说,则自不免于四者之病,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无所疑哉?”
“以百里而王天下,德之盛也。行一不义、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,心之正也。圣人之所以为圣人,其本根节目之大者,惟在于此。于此不同,则亦不足以为圣人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