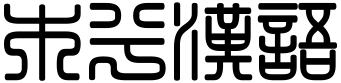公都子说:“外面的人都说先生喜欢您辩论,请问这是为什么呢?”
孟子说:“我难道喜欢辩论吗?我是不得已(而辩论)啊。天下有人类以来很久了,太平一时,动乱一时。在尧的时候,(东流的水)水倒流(一样),在中国泛滥,陆地成为蛇和龙的居所,使老百姓无处安身;低地的人在树上做巢,高地的人挖洞穴而居。《尚书》说:‘洚水警告我们。’洚水就是洪水。于是让禹来治水。禹挖地而把水导流入海,把蛇和龙赶到多草的沼泽;水从大地上穿行而过,这就是长江、淮河。黄河、汉水。险阻远离了人类,害人的鸟兽消灭了,然后人才能在平地上居住。
“尧、舜死后,圣人之道衰落,暴君一代又一代地出现,他们毁坏房屋来开挖深池,使老百姓无处安身;荒废农田来建园林,使老百姓得不到吃穿。这时又出现荒谬的学说、暴虐的行为。园林、深池、沼泽一多,禽兽又聚集来了。到了商纣的时候,天下又大乱。周公辅佐武王杀掉纣,又讨伐奄国,三年后,杀掉奄国的国君,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了他。灭了五十个国家,把老虎、豹子、犀牛、大象赶到远方。天下人很高兴。《尚书》说:‘伟大而显赫啊,文王的谋略!伟大的继承者啊,武王的功烈!庇佑我们,启发我们,直到后代,使大家都正确而没有错误。’
“时世衰落,道义微茫,荒谬的学说和暴虐的行为又出现了,有臣子杀掉他的君主的,有儿子杀掉他的父亲的。孔子为此忧虑,写了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说的是天子的事情(纠正君臣父子的名分,褒贬诸侯大夫的善恶,)。所以孔子说:‘了解我的可以只凭《春秋》这部书了!怪罪我的也可以只凭《春秋》这部书了!’
“(如今)圣王不出现,诸侯放纵恣肆,隐居不仕的人横发议论,杨朱、墨翟的学说充满了天下。天下种种议论,不是归附杨朱,就是归附墨翟。杨氏讲的是‘为我’的道理,这叫不把君主当回事,墨氏讲的是‘兼爱’的道理,这叫不把父亲当回事。目中无父,目中无君,这是禽兽啊。公明仪说:‘厨房里有肥肉,马厩里有肥马,而百姓面黄肌瘦,野外有饿死的尸体,这好似率领着野兽来吃人啊!’杨、墨的学说不消灭,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发扬,这就是荒谬的学说在欺骗百姓,堵塞了仁义的道路。仁义的道路被堵塞,就导致带领禽兽吃人,人们之间互相残杀。我为此忧虑,因而捍卫古代圣人的学说,抵制杨、墨,驳斥荒诞的言论,使发布邪说谬论的人起不来。种种邪说谬论从心里产生,就会妨害行动;妨害了行动,也就妨害了政治。即使有圣人再起,也不会改变我的这番话。
“从前禹平息了洪水而天下太平,周公兼并了夷狄,赶跑了猛兽而使百姓安宁,孔子作成了《春秋》而叛乱的臣子、作逆的儿子感到害怕。《诗经》说:‘戎狄是要防范的,荆舒是要严惩的,那就没有人能抗拒我。’目中无父、目中无君,是周公所防范的。我也要端正人心,抑制邪说谬论,反对偏激的行为,驳斥荒诞的言论,来继承这三位圣人。我难道喜欢辩论吗?我是不得已啊。能够用言论来反对杨朱、墨翟的,也就是圣人的门徒了。”
公都子:孟子弟子。
营窟:土屋,穴居。
洚(jiàng)水警馀:《尚书》逸篇里的话。洚水:大水。
菹(zū):水草多的沼泽地。
代作:更代而作,不断出现。污池:蓄水的池子。
伐奄三年讨其君:这是周成王时的事。飞廉:传说中善跑的人,为纣王所用。
《书》曰:以下所引,见今本《尚书·周书·君牙》。
丕:宏大。谟:谋略。承:继承。烈:功绩,事业。
有:通“又”。
《春秋》:古代编年体史书,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。
处士:不做官而居家的士人。杨朱:战国时魏人,晚于墨翟,早于孟子。墨翟,战国时鲁人,或说宋人,学说详见《墨子》。
闲:防御,捍卫。
承:抵抗。引诗出自《诗经·鲁颂·阔宫》。
孟子辩论高超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但是,孟子一方面承认自己多论辩,一方面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,并非喜欢。他把自己比作治水的大禹,之所以治洪水,是为百姓的安居。他把自己比作周公,之所以辅佐武王平定天下,为的是百姓才安宁、高兴。他把自己比作孔子,著《春秋》,做天子做的事,是要让“乱臣贼子惧”,为让纲常有序,天下太平。那么自己的论辩是为了端正人心,抑制邪说谬论,反对偏激的行为,驳斥夸诞的言论,怎么能说是喜欢辩论呢。
当时的背景是,杨子墨子的学说充满天下。杨子主张“为我”,孟子认为这是“无君”。墨子主张“兼爱”,把天下的父母都当自己的父母,不分亲疏远近,孟子认为这是“无父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孔子的仁义学说反而得不到发扬,结果就是天下不可能安宁。万般无奈之下,孟子也只有论辩,只有挺身而出反对杨墨学说。
孟子只是一介书生,但他是以大禹、周公、孔子三位圣人的继承者自许的。由此,我们不仅可以知道孟子爱论辩从何而来。
“盖邪说横流,坏人心术,甚于洪水猛兽之灾,惨于夷狄篡弑之祸,故孟子深惧而力救之。再言岂好辩哉,予不得已也,所以深致意焉。然非知道之君子,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?”
“盖邪说害正,人人得而攻之,不必圣贤;如春秋之法,乱臣贼子,人人得而讨之,不必士师也。圣人救世立法之意,其切如此。若以此意推之,则不能攻讨,而又唱为不必攻讨之说者,其为邪诐之徒,乱贼之党可知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