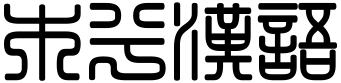匡章说:“陈仲子难道不是个廉洁的士人吗?住在于陵,三天没吃东西,饿得耳朵听不见,眼睛看不着。井上有个李子,被金龟子吃了大半,他爬过去,取来吃了三口,耳朵才听得见了,眼睛才看得着了。”
孟子说:“在齐国的士人中,我一定把陈仲子当作大拇指。尽管这样,仲子怎能算作廉洁呢?要扩充仲子的操守,那一定得当蚯蚓才可以。蚯蚓,在地上吃干土,在地下喝黄泉水(一切都不求人)。仲子所住的房子,是伯夷那样廉洁的人所建筑的呢?还是盗跖那样的强盗所建筑的呢?所吃的谷米,是伯夷那样廉洁的人所种的呢?还是盗跖那样的强盗所种的呢?这都是很难说的。”
匡章说:“这有什么关系呢?他亲自编织草鞋,他的妻子绩麻练麻,用它们来换取生活用品。”
孟子说:“陈仲子,是齐国的大家族。他的哥哥陈戴,从盖邑得的俸禄有几万石。他把哥哥的俸禄看作不义之禄而不吃,把哥哥的房屋看作不义之室而不住。避开哥哥,离开母亲,住在于陵。有一天回家,有个人送给他哥哥一只活鹅,仲子就皱缩着眉鼻说:‘哪里用得着这个嗷嗷叫的东西?’过些时候,他的母亲杀了这只鹅,给他吃。他的哥哥从外面回来,说:‘这就是那嗷嗷叫的东西的肉呀。’仲子出去吐掉了。母亲的东西不吃,妻子的东西就吃;哥哥的房子不住,于陵的房子就住。这还能算扩充操守吗?像仲子这样的人,只有变成了蚯蚓才能扩充他的操守呢。
匡章:战国时期齐国将军,曾率军拒秦,破燕,攻楚。
陈仲子:又称于陵仲子,战国时期齐国人,和孟子同时。
于(wū)陵:地名,在今山东长山南。
螬(cáo):蛴螬,金龟子的幼虫。将:取。
巨擘(bò):大拇指。这里比喻杰出的人物。
黄泉:指地下的泉水。
辟:同“避”;绩麻。纑(1ú):练麻。辟纑指将绩过的麻搓成线。
盖(gě):地名,陈戴的采邑。
辟:同“避”。
频顣(cù):又作“颦蹙”,紧皱眉头,表示不高兴的样子。
匡章认为陈仲子是个廉洁之士,他举了个典型的证据:陈仲子住在于陵,三天没吃东西,耳朵听不见了,眼睛也看不见了。井边有个被金龟子吃剩的半边李子,陈仲子吃了三口,然后才有听觉和视觉。陈仲子是齐国的宗族士家,有的是世代相传的禄田,他还不廉洁吗?
但是孟子却认为,这不是真正的廉洁,这只是蚯蚓的作为。如果推广陈仲子的这种廉洁,那就只有把人变成蚯蚓才行。按照孟子的观点,“食、色,性也”,饮食和男女交媾,这是人的天性。违反人的天性,有食物也不吃,这是一种病态的“廉洁”,不值得推广。
“仲子以母之食、兄之室,为不义而不食不居,其操守如此。至于妻所易之粟,于陵所居之室,既未必伯夷之所为,则亦不义之类耳。今仲子于此则不食不居,于彼则食之居之,岂为能充满其操守之类者乎?必其无求自足,如丘蚓然,乃为能满其志而得为廉耳,然岂人之所可为哉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