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子的处世方式是:不论是身处乱世而隐居,还是身处治世而大显身手,虽然“显”“隐”不同,但在诚心为社会为百姓做些好事这点上却是相同的。假如并无济世助人之心,而只是一味地跟着人家去“显”去“隐”,那你得不到世人的重视也是必然的。一个人在世而得不到世人的重视,便与草木差不多。菊是草木中一种不很起眼的花草,即使不露也是君子,枯死后也不会对不起自己的名声。因它对世人有所帮助,被称君子;而不想帮助世人的,则不是君子,甚至连草木都不如。一个真君子,哪能处于连草木都不如的境地?如果真的这样,便是真君子的羞耻。草木与人,相差很大,但做好事与不做,就是很显露也不是特别高尚。况且隐藏于山林邱壑之中,老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也没什么意义。
而我一个姓朱的朋友一世精通医道,总想帮助别人,起名菊隐。菊是一种花草木,是不很值钱的花草,虽无惊人之貌,但的确是真君子(菊兰竹梅乃花草四君子),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名气,朱君,是真君子,诚心要做好事,功夫了得,名气很大,他可不是混杂与世的人,但是他能尽自己微薄的力量,善做好事,从不对人提及自己的名气。其心地很是善良。盖菊是使人长寿的花草,在南阳种甘谷的事情已经验证过了。而医道是为人治病,让人长寿的,医术是延年增寿的学问,需借助草木来执行,非隐士不能精通这些草木。朱君用菊花等草药默默地给人看病,并说:“我是用菊花等草药看病而成名的”。续说:“我得名于菊,也深受菊名之累,何谈什么隐显之类的话。”馀接着说:“朱君和馀,是好朋友,君善于医术,而馀则喜欢饮酒,对菊下酒是很开心的事情,世人都知道陶渊名和刘伯伦等人。”因此还画下对菊令酒图,以做为记录。
南阳甘谷之事:相传南阳甘谷生长的菊花能使人延年益寿。
刘伯伦:刘伶,字伯伦,西晋竹林七贤之一,性嗜酒。
几千年来,孔孟所谓“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”(《论语,泰伯》)。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顾天下”(《孟子,尽心上》)的处世思想,似乎已经深深渗入中国士大夫的人格精神中。即便很有些蔑视礼教的唐寅也不例外。他的这篇《菊隐记》,便弥漫着很浓的孔孟气息。
作者提出“君子之处世”,无论显隐,“而其存心济物”,则应贯一始终。继而又指出,一个人若无济物救世的心志,而只是一浑然泛然的俗夫,于隐显之间全无自觉,自然会在纭纭世间销声匿迹,低微的如同草木,甚至连草木都不如。
显隐的故事,屡见于中国的史籍。大凡真正的隐士,仍是胸怀济物之心的。唯其如此,才为世人所敬重和仰慕。在唐寅看来,“存心济物”是士大夫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根本,若无此心志,“则虽显者,亦不足贵,况隐于山林丘壑之中者耶”?
唐寅的朋友朱大浸并非官位显赫的贵介,而只是一个隐于民间的君子,然而他“世精疡医,存心济物”,是一个不同凡响的高蹈之士。唐寅由他的人品医术,而赞慕他的号“菊隐”,因为“菊隐”两字的内涵确实包蕴了处于江湖的中国士大夫阶层(自然包括唐寅)内心孤高清芬的意味。诚然,菊没有牡丹那份“花开时节动京城”的“好颜色”和富贵艳紫气,它总是同潇潇秋雨,飒飒秋风相联系,但在中国古代士人的心目中,却透出那种孤高雅洁,清芬沁人的山林旨趣,尤为退离仕宦的人士所喜爱。唐寅说它“生必于荒铃郊野之中,唯隐者得与之近,就更突出了它的高洁之性。朱君以医行道,”其功甚大,其名甚著“,却毫不爱恋牡丹的宫廷脂粉气,而一心仰慕菊的那份山林荒野气,从中可以透视他内心的精神品格,而这正是作者自己的襟怀胸臆。
唐寅在文末说:“君隐于菊,而馀也隐于酒。对菊令酒,世必有知陶渊明,刘伯伦者矣。”他们胸存济物之心而无以报国,行饮山水,笑傲江湖的内心体味,正是唐寅所要叹发的感慨,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精神生活的写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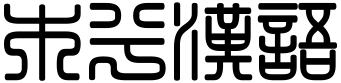
《菊隐记》是明代文学家唐寅所作的一篇散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