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明柳暗,忧愁绕着天时转。登上了高高城楼,又上高楼。
要想问孤飞的鸿雁,你将飞向何方?岂不知自己的身世,同样悠悠茫茫!
夕阳楼:旧郑州之名胜,始建于北魏,为中国唐宋八大名楼之一,曾与黄鹤楼、鹳雀楼、岳阳楼等齐名。
荥阳:在河南省郑州市荥阳一带。
是:指夕阳楼。
所知:所熟悉的人。
萧侍郎:即萧澣。《旧唐书·文宗纪》:“大和七年三月,以给事中萧澣为郑州刺史,入为刑部侍郎。九年六月,贬遂州司马。”《地理志》:“遂州遂宁郡,属剑南东道。”萧澣贬遂州司马,不久病逝,李商隐作有《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》。
花明:九月繁花凋谢,菊花开放,特别鲜明。
柳暗:秋天柳色深绿,显得晦暗。
绕天愁:忧愁随着天时循环运转而来,秋天有秋愁。
重城:即“层楼”,指高高的城楼。
楼:指夕阳楼。
这首诗以眼前看到的景物入手,以艺术的手法来诠释心中的愁绪和感慨,读起来沉郁真挚,依稀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幅花明柳暗、高楼独立、孤鸿飞翔的画面。李商隐用他生动的笔墨,既写出了夕阳楼的真实风景,也尽情倾诉了他的心事和渴望。
“首两句”是倒装语。“花明柳暗”的风景是在“上尽重城更上楼”后所见。但第二句对于第三句的“欲问孤鸿向何处”,又是顺叙。可见诗人构思炼句之巧妙。像《登乐游原》一样,诗人的身心异常疲累,灵与肉遭受着痛苦的煎熬,心灵的宇宙愁云密布,内心深处感到异乎寻常的压抑与孤独。所以诗人“上尽重城更上楼”时,不愿,不甘,乏力,又无可奈何,“上尽”,还要“更上”,成了一种负担,一种难以承受的体力和精神的负担。这与王之涣“更上一层楼”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。诗人登楼所见景物有二:一曰花明柳暗。二曰悠悠孤鸿。众所周知,任何诗人描摹景物,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审美选择,并把选择对象在自己的心灵中加以主观化的熔铸。成为诗人自己的经过改造了的景物。《夕阳楼》诗中所出现的“花明柳暗”,说明时值春色烂漫的季节,大自然本应是一派生机盎然的天地。但是李商隐却没有“峰回路转”、“又一村”的那种感觉,而是把弥漫在诗人自己胸际黯淡的愁云,又转而弥漫到“花明柳暗”的景物之上,使如许春色也蒙上了一层万里愁云万里凝的黯淡色彩,而且诗人胸际的愁云又放而大之,弥漫充塞到了天地间,成了“绕天愁”,此愁不同于它愁,此愁悠长、纷乱。李商隐诗在遣词造句上是非常讲究的,同一事物,他不说“柳暗花明”,而写成“花明柳暗”,词序排列由明而暗,而愁,以显出情绪变化的层次,如按通常“柳暗花明”的说法,便乱而无序了。由此可见诗人对意象的关注,造境的巧妙。
诗中三、四两句专就望中所见孤鸿南征的情景抒慨。仰望天空,万里寥廓,但见孤鸿一点,在夕阳馀光的映照下孑然逝去。这一情景,连同诗人此刻登临的夕阳楼,都很自然地使他联想起被贬离去、形单影只的萧澣,从内心深处涌出对萧澣不幸遭际的同情和前途命运的关切,故有“欲问”之句。但方当此时,忽又顿悟自己的身世原来也和这秋空孤鸿一样孑然无助、渺然无适,真所谓“不知身世自悠悠”了。这两句诗的好处,主要在于它真切地表达了一种特殊人生体验:一个同情别人不幸遭遇的人,往往未有意识到他自己原来正是亟须人们同情的不幸者;而当他一旦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时,竟发现连给予自己同情的人都不再有了。“孤鸿”尚且有关心它的人,自己则连孤鸿也不如。这里蕴含着更深沉的悲哀,更深刻的悲剧。冯浩说三四两句“凄惋入神”,也许正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。而“欲问”、“不知”这一转跌,则正是构成“凄惋入神”的艺术风韵的重要因素。此诗体现了李商隐七绝“寄托深而措辞婉”(叶燮《原诗》)的特点。
谢枋得:夕阳不好说,此诗形容不着迹。孤鸿独飞,必是夕阳时;若只道身世悠悠,与孤鸿相似,意思便浅。“欲问”、“不知”,四字无限精神。(《叠山诗话》)
徐充曰:身无定居,与鸿何异?此因登夕阳楼感物而兴怀也。胡次焱注:身世方自悠悠,而问孤鸿所向,不几于悲乎?“自”字宜玩味。我自如此,何问鸿为?感慨深矣。焦竑曰:感慨无穷。此与“最无根蒂是浮名”同例,驰竞者诵之,可以有省。(《唐诗选脉会通评林》)
纪昀:“借孤鸿对写,映出自己,吞吐有致,但不免有做作态,觉不十分深厚耳。”(《玉溪生诗说》)
冯浩:“自慨慨萧,皆在言中,凄惋入神。”(《玉溪生诗集笺注》)
刘学锴、馀恕诚:“三四巧于言情,不直言己之身世如悠悠孤鸿,而谓方将同情孤鸿之远去,忽悟己之身世亦复如彼。是怜人者正须被怜,而竟不自知其可怜,亦无人复怜之也。运思固极婉曲,言情亦极凄惋,然浑朴之气亦因之而斫削。纪评虽稍苛,然眼力自非张氏之一味吹捧者可比。”(《李商隐诗歌集解》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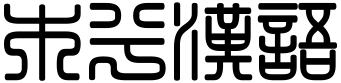
《夕阳楼》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作品,作于唐文宗大和九年秋天。作者的知己萧澣被贬,诗人登夕阳楼(此楼为萧澣在郑州刺史任上所建),触景伤情,感慨万千,写下这首情致深婉的小诗。此诗以眼前看到的景物入手,依稀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幅花明柳暗、高楼独立、孤鸿飞翔的画面,以艺术的手法来诠释心中的愁绪和感慨。尤其是后二句,蕴含着更深沉的悲哀,更深刻的悲剧,让全诗达到凄惋入神的境界,体现出无限的诗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