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龙吟:词牌名。出自李太白诗句「笛奏龙吟水」。又名《龙吟曲》、《庄椿岁》、《小楼连苑》。《清真集》入「越调」。各家格式出入颇多,兹以历来传诵苏辛两家之作为准。。一百零二字,前后片各四仄韵。又第九句第一字并是领格,宜用去声。结句宜用上一、下三句法,较二、二句式收得有力。
参差是:差不多如此。唐·白乐天《长恨歌》:「中有一人字太真,雪肤花貌参差是。」
凛然生气:南朝宋·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:「庾道季云:『廉颇、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,懔懔恒如有生气。曹蜍、李志虽见在,厌厌如九泉下人。人皆如此,便可结绳而治,但恐狐狸貒貉啖尽。』」
高山流水:用伯牙、钟子期相知事。伯牙善琴,寓情高山流水,惟子期为知音。子期死,伯牙终身不复抚琴。此谓以高山流水为知音。《列子·卷五·〈汤问·高山流水〉》:「伯牙善鼓琴,钟子期善听。伯牙鼓琴,志在登高山。钟子期曰:『善哉!峨峨兮若泰山!』志在流水。钟子期曰:『善哉!洋洋兮若江河!』伯牙所念,钟子期必得之。伯牙游于泰山之阴,卒逢暴雨,止于岩下;心悲,乃援琴而鼓之。初为霖雨之操,更造崩山之音。曲每奏,钟子期辄穷其趣。伯牙乃舍琴而叹曰:『善哉,善哉,子之听夫!志想象犹吾心也。吾于何逃声哉?』」
「富贵他年,直饶未免」句:南朝宋·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:「初,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,兄弟已有富贵者,翕集家门,倾动人物。刘夫人戏谓安曰:『大丈夫不当如此乎?』谢乃捉鼻曰:『但恐不免耳!』」直饶,「即使」之意。
「甚东山何事,当时也道,为苍生起」句:南朝宋·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:「谢公在东山,朝命屡降而不动。后出为桓宣武司马,将发新亭,朝士咸出瞻送。高灵时为中丞,亦往相祖。先时,多少饮酒,因倚如醉,戏曰:『卿屡违朝旨,高卧东山,诸人每相与言:「安石不肯出,将如苍生何?」今亦苍生将如卿何?』谢笑而不答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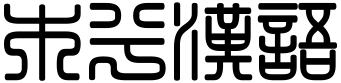
辛稼轩自青少年时代起,就饱经战乱之苦,立志抗金,恢复中原,他的词也以激越豪放而著称。但是在这首《水龙吟》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,却引归耕隐居的陶渊明为「知己」,未免有点消极。之所以如此,与他的遭际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据学者考证,此词约作于光宗绍熙五年(西元一一九四年),那年辛稼轩已经五十五岁,秋天又被罢官,于是感伤世事人生,不免慨叹。
此词上阕开头就说:「老来曾识渊明,梦中一见参差是。」句法就有点特别。陶渊明与作者,本来志趣不同,性格各异,而作者却说他们已有了神交,并在梦中见过面了。这对一般读者来说,不能不感到突兀、惊诧,从而也就有可能构成一个强烈的印象,令人玩味。「老来」二字是特指,说明作者驱驰战马、奔波疆场或是筹划抗金、收复故土的年轻时代,与脱离尘嚣、回归自然的陶渊明是无缘的,而只有在他受到压抑与排斥,壮志难酬的老年时代,才有机会「相识渊明」。这个开头,对读者来说既有些突然,又让人感到十分自然。而作者也以平静的语气叙述,益发显得深沉。接下去的「觉来幽恨,停觞不御,欲歌还止」三句,直接抒写作者心中的沉痛心情。心头之恨是如此沉重,竟使得作者酒也不饮,歌也不唱。这是为什么?作者作了回答:一个白发老翁怎能在西风萧瑟中为五斗米折腰!但是,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。
词的下阕紧随前文,并作了更深入的回答:悔恨东山再起!先讲陶渊明的精神、人格和事业都是永在的,而且仍凛然有生气,和现实是相通的。「懔然生气」一句,这里暗用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「廉颇、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,懔懔恒如有生气」的语言以赞渊明。正是因为如此,所以作者紧跟着又用了「高山流水」的典故,来说明他同渊明之间是千古知音。这知音就在于对「富贵他年」所持的态度。接下去「富贵他年,直饶未免,也应无味」三句,引用了东晋谢安的故事。据《世说新语·排调篇》记载:「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,兄弟已有富贵者,翕集家门,倾动人物。刘夫人戏谓安曰:‘大丈夫不当如此乎?’谢乃捉鼻曰:‘但恐不免耳。’」说明即使他年不免于富贵显达,也是没有意思的。结语「甚东山何事」三句用的仍然是谢安的事,同书又记载:「谢公在东山,朝命屡降而不动。后出为桓宣武司马,将发新亭,朝士咸出瞻送。高灵时为中丞,亦往相祖。先时多少饮酒,因倚如醉,戏曰:‘卿屡违朝旨,高卧东山,诸人每相与言:安石不肯出,将如苍生何?今亦苍生将如卿何?’谢笑而不答。」很显然,从作者到陶渊明,又从陶渊明到谢安,或富贵显达,或归田隐居,或空怀壮志,虽处境各不相同,但其实一样,都没有什么意义。这是英雄的悲叹。
与辛稼轩其他一些诗词中所反映出来的豪情壮志不同,在这首词中,作者已没有「要挽银河仙浪,西北洗胡沙」(《水调歌头》),「道男儿到死心如铁,看试手,补天裂」(《贺新郎》)那种壮志凌云、激越慷慨的感情,而是把一切都看得如此闲淡无谓,如此的不屑一顾,这绝不是作者的本意,而是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哀叹,是时代的悲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