乘船西归,天天逆风而行,憔悴归来犹如古人邴曼容。郑贾想买的是死老鼠而不是玉石,叶公喜欢的是雕刻的龙而非真龙。
今后无事唯有饮酒,且把青松当作挚友相陪。如果梦中遇到曹孟德,也只有相对言老了。
瑞鹧鸪:《宋史·乐志》入「中吕调」,元高拭词注「仙吕调」。《苕溪词话》云:「唐初歌词,多五言诗,或七言诗,今存者止《瑞鹧鸪》七言八句诗,犹依字易歌也。」据《词谱》说,《瑞鹧鸪》原本七言律诗,因唐人用来歌唱,遂成词调。冯正中词名《舞春风》,陈永年词名《桃花落》,尤遂初词名《鹧鸪词》,元丘长春词名《拾菜娘》,《乐府纪闻》名《天下乐》。《梁溪漫录》词有「行听新声太平乐」句,名《太平乐》;有「犹传五拍到人间」句,名《五拍》。此皆七言八句也。至柳屯田有添字体,自注「般涉调」,有慢词体,自注「南吕宫」,皆与七言八句者不同。此调始于五代冯正中《舞春风》词,清人沈辰垣《历代诗馀·卷三十二》录之,注云:「《瑞鹧鸪》,五十六字,一名《舞春风》,一名《鹧鸪词》,通首皆平韵,与七言近体诗无异。若用仄韵,即系《玉楼春》、《木兰花》调也。」近代学者任半塘《教坊记笺订·大曲名》中「舞春风」条下注:「五代杂曲之《舞春风》,乃七言八句声诗体,所谓《瑞鹧鸪》是也。」《瑞鹧鸪》填制盛于宋代。《宋史·乐志》载:「太宗洞晓音律,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,总三百九十。……因旧曲造新声者五十八:仙吕调《倾杯乐》、《月宫仙》、《戴鲜花》、《三台》;中吕调《倾杯乐》、《菩萨蛮》、《瑞鹧鸪》、《三台》。」全宋词有《瑞鹧鸪》词目六十五条,作者三十馀人,多咏物、酬唱作答、抒情、祝寿等;衰于金元,全金元词有《瑞鹧鸪》词目八十一条,几为全真教人之作。词作数量虽逾前代,然词作内容皆为传教布道,同时作者人数亦大不如宋。此调本律诗体,七言八句,宋词皆同。其小异者惟各句平仄耳。此词前后阕起句、结句第二字、第六字俱仄声,中二句第二字、第六字俱平声,惟陈永年词「尽出花钿散宝冿,云鬟初剪向残春。因惊风烛难留世,遂作池莲不染身。贝叶乍疑翻锦绣,梵声才学误梁尘。从兹艳质归空后,湘浦应无解佩人。」平仄同此。宋人如此填者甚少,皆照贺方回体填。
乙丑奉祠: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七五·三七》:「开禧元年七月二日,新知隆兴府辛弃疾与宫观,理作自陈。」
馀干:清·顾宛溪《读史方舆纪要·卷八十五·〈江西·饶州府·馀干县〉》:「馀干县,(饶州)府南百二十里。东至万年县六十里,东南至安仁县百二十里,东北至浮梁县二百六十里。春秋时为越之西界,所谓『干越』也。汉为馀汗县,属豫章郡。汗音『干』。后汉因之。三国吴属鄱阳郡,晋因之。刘宋改『汗』为『干』,齐梁仍旧。隋平陈,县属饶州。唐宋因之。元元贞初升为馀干州。明初复为县。旧有城,唐元和中筑,寻废。明嘉靖四十一年复营筑,隆庆初增修,万历八年又复葺治,城周三里。编户二百六十里。」
打头风:逆风也。宋·欧阳永叔《归田录·卷二》及宋·叶石林《避暑录话》俱谓「打」音「滴耿反」,则当读若「顶」,即今所称顶头风也。宋·欧阳永叔《归田录·卷二》:「今世俗言语之讹,而举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缪者,惟『打』字尔。(打,『丁雅反』)其义本谓『考击』,故人相欧、以物相击,皆谓之『打』,而工造金银器亦谓之『打』可矣,盖有『槌一作「挝」击』之义也。至于造舟车者曰『打船』『打车』,网鱼曰『打鱼』,汲水曰『打水』,役夫饷饭曰『打饭』,兵士给衣粮曰『打衣粮』,从者执伞曰『打伞』,以糊黏纸曰『打黏』,以丈尺量地曰『打量』,举手试眼之昏明曰『打试』,至于名儒学,语皆如此,触事皆谓之『打』,而遍检字书,了无此字。(『丁雅反』者)其义主『考击』之『打』,自音『谪疑当作滴耿』,以字学言之,打字从手、从丁,丁又击物之声,故音『谪耿』为是。不知因何转为『丁雅』也。」宋·叶石林《避暑录话·卷下》:「欧阳文忠记『打』音本『谪耿切』,而举世讹为『丁雅切』,不知今吴越俚人,正以相殴击为『谪耿』音也。」
邴曼容:《汉书·卷七十二·〈王贡两龚鲍列传·两龚传〉》:「琅邪邴汉亦以清行征用,至京兆尹,后为太中大夫。……汉兄子曼容亦养志自修,为官不肯过六百石,辄自免去,其名过出于汉。」此处自比邴曼容,言官职不高,且免去也。
「郑贾正应求死鼠」句:谓朝廷所需未必是真人才,而是符合朝廷标准框定之「人才」。《战国策·卷五·〈秦策三·应侯曰郑人谓玉未理者璞〉》:「应侯曰:『郑人谓玉未理者『璞』,周人谓鼠未腊『朴』。周人怀璞过郑贾曰:『欲买朴乎?』郑贾曰:『欲之。』出其朴,视之,乃鼠也。因谢不取。今平原君自以贤,显名于天下,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。天下之王尚犹尊之,是天下之王不如郑贾之智也,眩于名,不知其实也。』」
「叶公岂是好真龙」句:西汉·刘中垒《新序·卷五·杂事》:「子张见鲁哀公,七日而哀公不礼,托仆夫而去曰:『臣闻君好士,故不远千里之外,犯霜露,冒尘垢,百舍重趼,不敢休息以见君,七日而君不礼,君之好士也,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。叶公子高好龙,钩以写龙,凿以写龙,屋室雕文以写龙,于是夫龙闻而下之,窥头于牖,拖尾于堂,叶公见之,弃而还走,失其魂魄,五色无主,是叶公非好龙也,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。今臣闻君好士,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,七日不礼,君非好士也,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。诗曰:「中心藏之,何日忘之。」敢托而去。』」
「孰居无事陪犀首」句:《史记·卷七十·〈张仪传·(附)犀首传〉》:「犀首者,魏之阴晋人也,名衍,姓公孙氏。与张仪不善。」《史记·卷七十·〈张仪传·(附)陈轸传〉》:「陈轸者,游说之士。与张仪俱事秦惠王,皆贵重,争宠。……居秦期年,秦惠王终相张仪,而陈轸奔楚。楚未之重也,而使陈轸使于秦。过梁,欲见犀首。犀首谢弗见。轸曰:『吾为事来,公不见轸,轸将行,不得待异日。』犀首见之。陈轸曰:『公何好饮也?』犀首曰:『无事也。』」《庄子·卷十四·〈外篇·天运〉》:「孰居无事,推而行是?」
「未办求封遇万松」句:《汉书·卷九十九上·王莽传》:「(居摄元年)四月,安众侯刘崇与相张绍谋曰:『安汉公莽专制朝政,必危刘氏。天下非之者,乃莫敢先举,此宗室耻也。吾帅宗族为先,海内必和。』绍等从者百馀人,遂进攻宛,不得入而败。绍者,张竦之从兄也。竦与崇族父刘嘉诣阙自归,莽赦弗罪。竦因为嘉作奏曰:『……愿为宗室倡始,父子兄弟负笼荷锸,驰之南阳,猪崇宫室,令如古制。……』于是莽大说。公卿曰:『皆宜如嘉言。』莽白太后下诏曰:『惟嘉父子兄弟,虽与崇有属,不敢阿私,或见萌牙,相率告之,及其祸成,同共雠之,应合古制,忠孝著焉。其以杜衍户千封嘉为师礼侯,嘉子七人皆赐爵关内侯。』后又封竦为淑德侯。长安谓之语曰:『欲求封,过张伯松;力战斗,不如巧为奏。』莽又封南阳吏民有功者百馀人,汙池刘崇室宅。后谋反者,皆汙池云。」按:竦字伯松,词中作「万松」,不知何故。
「却笑千年曹孟德,梦中相对也龙钟」句:其意或为:曹孟德所作《龟虽寿》中虽有「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」之句,然与之梦中相遇,却已是老态龙钟之衰翁。稼轩盖藉此为自身暮之出处遭遇解嘲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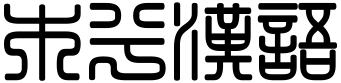
《瑞鹧鸪·乙丑奉祠归,舟次馀干赋》是辛稼轩于宋宁宗开禧元年(西元一二〇五年)被劾免职,从京口返铅山,舟行途经馀干县境时所作。
开禧元年六月,韩侂胄还在准备北伐,稼轩本年春以举荐不当连降两官。稼轩知镇江府方一年,北伐准备工作纔刚刚开始,南宋朝廷也正在下令给前线各地驻军,让他们秘密制订进攻计划的当口,却突然改稼轩知隆兴府,乾脆将他从前线调离了。在稼轩还没有离开镇江赴任隆兴时,韩伲侂胄一派的言官再以「好色、贪财、淫刑、聚敛」劾稼轩而免职。稼轩离京口返铅山,舟行途经馀干县(今江西馀干县,位于鄱阳湖南岸),遂作《瑞鹧鸪·乙丑奉祠归,舟次馀干赋》。
此词写于作者被强行授予宫祠。令其自省回归铅山途中,其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。词中反复讲说的一个中心,便是朝廷不识真正的人才——自己并没有任何错谬,竟无端遭此贬退。上阕首句以「打头风」开篇,,喩世路艰难。下句承接的便是「憔悴归来邴曼容」; 归来是「憔悴归来」, 很显然不属于正常的离任。随后以郑贾求鼠、叶公好龙两个典故,意在说明当今主事者大谈人才,完全是一片虚伪。古往今来, 当权者每个都会惊呼「人才难得」, 然而真有人才脱颖而出时, 却没有几个能容下他们。所以前贤早有卓见:历史上最能人尽其才的时代,都是战乱纷扰的时代, 因为那时不用人才,连他自身都无法保住了。「孰居无事陪犀首,未办求封遇万松」将犀首「无事好饮」一典及《庄子·天运》「孰居无事」一语联用,以表达自己老年罢官、抗金事业无成之后极度灰心失望的情绪和无事可作的现状。和平时日, 大多岗位尸位素餐,越庸俗的人越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。等到这群硕鼠把王朝掏空了,当权者纔又想到「人才」,这几乎是历朝历代不可避免的规律,绝不仅仅是稼轩那个时代。不少人说,三国时期的人才都能得到重用,不论是谋臣还是降将,所以作者提到曹孟德,然而孟德如果生在今日,谅他也未必找得到一展雄才的机会。
整首词藉古喩今,用典甚多,字少言多,抒发英雄暮年失落的愤懑、感伤等情绪。表达了作者自己英雄年老、罢官失落、抗金事业无成之后极度愤懑、失望的情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