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年谢安隐居在东海,出仕做官鬓发已霜秋,中年难与亲友别,唯有丝竹缓离愁。一旦功成名就,准备返归东海,谁料抱病入西州。做官困扰了隐居的雅志,遗恨寄托于田园山丘。
既已年高衰朽,便当及早划筹,要做百姓穿粗裘。返回故乡遵迢千里,选取佳地长住久留。酒醉放歌君相和,醉倒在地君扶我,只有醉时忘忧愁。任凭刘备笑我无大志,我却甘愿身居平地,仰看他高卧百尺楼。
水调歌头:词牌名。调名来源自《水调》曲。《水调》曲,隋炀帝所制也。唐·刘鼎卿《隋唐嘉话》:「炀帝凿汴河,自制《水调歌》。」宋·王颐堂《碧鸡漫志·卷四·〈水调歌〉》引《脞说》:「《水调》《河传》,炀帝将幸江都时自制,声韵悲切,帝喜之。乐工王令言谓其弟子曰:『不返矣,《水调》《河传》但有去声。』」《〈樊川诗集〉注·卷三·〈扬州〉诗》「谁家唱《水调》」句自注亦云:「炀帝凿汴河成,自造《水调》。」然《水调》究制于开汴河前或汴河开成后,三家说法不一,但为炀帝自制,则无异辞。逮唐,《水调》已为传唱不衰之名曲。盛唐王龙标有《听流人〈水调子〉》诗:「岭色千重万重雨,断弦收与泪痕深。」唐·段安节《乐府杂录·歌》:「开元中,内人有许和子者,本吉州永新县乐家女也,开元末选入宫,即以永新名之,籍于宜春院。既美且慧,善歌,能变新声。……洎渔阳之乱,六宫星散,永新为一士人所得。(金吾将军)韦青避地广陵,因月夜凭阑于小河之上,忽闻舟中奏《水调》者,曰:『此永新歌也。』乃登舟与永新对泣久之。青始亦晦其事。」可见《水调》为时人所熟。玄宗本人亦喜听此曲,奔蜀之前,登楼置酒,令善唱《水调》者登楼而歌,「闻之,潸然出涕」(唐·李朱崖《次柳氏旧闻》,唐·郑延美《明皇杂录》)。中唐白乐天有《听〈水调〉》诗:「不会当时翻曲意,此声肠断为何人?」晚唐罗昭谏亦有《席上歌〈水调〉》:「若使炀皇魂魄在,为君应合过江来。」至五代北宋,《水调》仍在传唱。宋·郑仲贤《南唐近事》载「(元宗)尝乘醉,命乐工杨花飞奏《水调辞》进酒。」南唐冯正中《抛球乐》亦有「《水调》声长醉里听」之句。北宋·张子野《天仙子》之「《水调》数声持酒听」更为人所熟。与子野同时而略晚的刘原甫《公是集》有《扬州闻歌》诗:「淮南旧有《于遮》舞,隋俗今传《水调》声。」一曲传唱四五百年,其魅力可见矣。唐时《水调》有大曲、小曲之分。大曲《水调》歌,「凡十一叠,前五叠为歌,后六叠为入破。其歌,第五叠五言调,声韵怨切。故白乐天诗云:『五言一遍最殷勤,调少情多似有因。不会当时翻曲意,此声肠断为何人?』」(《乐府诗集·卷七十九·〈水调〉歌》)按,《乐府诗集》所载十一叠《水调》,第一至第四叠(遍)歌为七言,第五叠为五言;入破第一至第五为七言,第六辙又为五言。《水调》小曲,为单曲歌唱参任半塘《唐声诗·下编卷十三》。王龙标所听《水调子》即是小曲。时《水调》主以笛奏,唐大曲《水调》第二叠歌辞即说「笛倚新翻《水调歌》」,冯正中《采桑子》:「《水调》何人吹笛声?」「唐又有新《水调》,亦商调曲也。」(《乐府诗集·卷七十九·〈水调〉歌》)《碧鸡漫志·卷四·〈水调歌〉》引白乐天《看采菱》诗所言「时唱一声新《水调》,谩人道是《采菱歌》」,即指「《水调》中新腔」。唐代《水调》,又指音调名,即一部乐之总名非一曲之专名。《唐会要·卷三十三》所载「南昌商,时号『水调』」,即指音调而言。《碧鸡漫志·卷四·〈水调歌〉》:「《理道要诀》所载唐乐曲,南吕商时号『水调』。予数见唐人说『水调』,各有不同。予因疑『水调』非曲名,乃俗呼音调之异名,今决矣。……《外史梼杌》云:『王衍泛舟巡阆中,舟子皆衣锦绣,自制水调《银汉曲》。』此『水调』中制《银汉曲》也。」王衍所制《银汉曲》,属「水调」乐部中之曲,故《银汉曲》前冠以「水调」。毛稚黄《填词名解·卷三》据此亦云:「水调者,一部乐之名也;《水调歌》者,一曲之名也。」《水调歌头》则是截取大曲《水调》之首章另倚新声而成。《填词名解》:「歌头,又曲之始音,如《六州歌头》、《氐州第一》之类。《海录碎事》云:『炀帝开汴河,自造《水调》,其歌颇多,谓之『歌头』,首章之一解也。顾从敬《诗馀笺释》云:『明皇欲幸蜀时,犹听唱《水调》,至「唯有年年秋雁飞」,因潸然,叹峤真才子!不待曲终。』水调曲颇广,因歌止首解,故谓之『歌头』。或云南唐元宗留心内宠,击鞫无虚日。乐工杨花飞奏《水调》词,但唱『南朝天子爱风流』一句,如是数四,以为讽谏。后人广其意为词,以其第一句,故称『水调歌头』云。」《水调歌头》与唐人《水调》所属宫调不同:唐《水调》,属商调曲;宋《水调歌头》,则为中吕调(《碧鸡漫志·卷四·〈水调歌〉》)。故《词谱·卷二十三》:「凡大曲歌头,另倚新声也。」毛东堂词名《元会曲》,张芸窗词名《凯歌》,吴梦窗词《江南好》,贺方回词名《台城游》,汪相如词名《水调歌》,薑白石词名《花犯念奴》,明杨升庵词名《花犯》。双调,九十五字,前后阕各四平韵。亦有前后阕两六言句夹叶仄韵者,有平仄互叶几于句句用韵者。
调注:傅子立注:「公旧序云:『馀去岁在东武,作《水调歌头》以寄子由。今年子由相从彭门居百馀日,过中秋而去,作此曲以别。馀以其语过悲,乃为和之,其意以不早退为戒,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。』」刘尚荣按:「子由所作『此曲』为《水调歌头·徐州中秋》。」《东坡外集》词末注:「此与曹炜『落日寒垣路』同调也,醉后思我,请令泸女歌之。」
彭门:龙榆生笺引《钦定大清一统志·卷六十九·徐州府》:「徐州府,《禹贡》徐州之域,古大彭氏国。春秋属宋为彭城邑。战国属楚。秦置彭城县。汉元年,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,都此(《货殖传》:『沛郡、汝南为西楚,彭城以东傅海为东楚,文颖曰:项羽都之,谓之西楚』);五年属汉,为楚国,地节元年改曰彭城郡;黄龙元年,复曰楚国。后汉章和二年,改曰彭城国。三国魏始移徐州来治。晋亦曰徐州彭城国,义熙七年改曰北徐州。宋永初二年,复曰徐州彭城郡。后魏因之。北齐置东南道行台。后周置总管府。隋开皇初郡废,七年行台废;大业四年,府废,复曰彭城郡。唐武德四年,复曰徐州兼置总管府;贞观十七年,府罢;天宝初,复曰彭城郡;乾元初,复曰徐州属河南道(《唐书·方镇表》:『建中二年,置徐海沂密都团练观察使,治徐州。兴元元年,废。贞元四年,置徐泗濠三州节度使,治徐州。十六年废。』);元和二年,置武宁军节度使;咸通三年,罢;十一年,改置感化军节度。五代晋复曰武宁军。宋亦曰徐州彭城郡武宁节度使,属京东西路。金属山东西路,贞祐三年,改隶河南路。元至元二年,省彭城县,入之降为下州,属归德府;至正八年,升徐州路;十二年降为武安州。明初复曰徐州属凤阳府;八年属南直隶。」
「安石在东海,从事鬓惊秋」句:傅子立注:「晋谢安字安石,少栖迟东土,放情丘壑。及仕进之时,年已四十馀矣。」刘尚荣按:「事详《晋书·卷七十九·谢安传》。」龙榆生笺引《晋书·卷七十九·谢安传》:「谢安,字安石,……少有重名,……栖迟东土,……放情丘壑。……时安弟万为西中郎将,总籓任之重。安虽处衡门,其名犹出万之右,自然有公辅之望,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。安妻,刘惔妹也,既见家门富贵,而安独静退,乃谓曰:『丈夫不如此也?』安掩鼻曰:『恐不免耳。』及万黜废,安始有仕进志,时年已四十馀矣。」从事,《东坡外集》作「从仕」。
「中年亲友难别,丝竹缓离愁」句:傅子立注:「安石尝谓王羲之曰:『中年已来,伤于哀乐,与亲友别,辄作数日恶。』羲之曰:『年在桑榆,自然如此,顷只赖丝竹陶写,常恐儿辈觉,损欢乐之趣。』」刘尚荣按:「详见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、《晋书·卷八十·王羲之传》。」龙榆生笺引《晋书·卷八十·王羲之传》:「谢安尝谓羲之曰:『中年以来,伤于哀乐,与亲友别,辄作数日恶。』羲之曰:『年在桑榆,自然至此。顷正赖丝竹陶写,恒恐儿辈觉,损其欢乐之趣。』」
功成名就:傅子立注:「《老子》:『功成名遂身退,天之道。』」刘尚荣按:「句见河上公注《老子道德经·卷上·第九章》。王弼注《老子道德经·第九章》作『功成身遂天之道。』」
「准拟东还海道,扶病入西州」句:傅子立注:「安石东山之志始末不渝。及镇新城,欲经略粗定,即江道东还。志未就,遇疾。诏还都门,当入西州门,自以本志不遂,深自慨失,因怅然谓所亲曰:『吾病殆不起乎!』」刘尚荣按:「详见《晋书·卷七十九·谢安传》。」龙榆生笺引《晋书·卷七十九·谢安传》:「安虽受朝寄,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,每形于言色。及镇新城,尽室而行,造泛海之装,欲须经略粗定,自江道还东。雅志未就,遂遇疾笃。上疏请量宜旋旆,……诏遣侍中慰劳,遂还都。闻当舆入西州门,自以本志不遂,深自慨失,因怅然谓所亲曰:『昔桓温在时,吾常惧不全。忽梦乘温舆行十六里,见一白鸡而止。乘温舆者,代其位也。十六里,止今十六年矣。白鸡主酉,今太岁在酉,吾病殆不起乎!』乃上疏逊位,诏遣侍中、尚书喻旨。先是,安发石头,金鼓忽破,又语未尝谬,而忽一误,众亦怪异之。寻薨,时年六十六。」
困轩冕:明刊《苏集》、《苏长公二妙集》本作「因轩冕」。傅子立注:「一作『傲轩冕』。」龙榆生笺:「《庄子·缮性》:『今之所谓得志者,轩冕之谓也。轩冕在身,非性命也,物之傥来,寄者也。』张曲江《商洛山行怀古》诗:『避世辞轩冕,逢时解薜萝。』」
沧洲:傅子立注引唐·杜子美《奉赠卢五丈参谋琚(jū)》诗:「辜负沧洲愿。」刘尚荣按:「原作『沧州』,傅注引杜诗亦作『沧州』,今据元延祐本及《杜诗详注》改。按『沧州』,地名,与词旨无涉;「沧洲」谓海滨,隐士居处也,与『安石在东海』意暗合。」
褐裘:傅子立注引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:「无衣无褐,何以卒岁?」又引扬子《法言·卷七·寡言》:「大寒而后索衣裘,不亦晚乎?」
「惟酒可忘忧」句:傅子立注:「晋顾荣谓张翰曰:『惟酒可以忘忧,但无如作病何耳!』」刘尚荣按引《晋书·卷七十八·顾荣传》:「顾荣,字彦先,吴国吴人也,为南土著姓。……恒纵酒酣畅,谓友人张翰曰:『惟酒可以忘忧,但无如作病何耳。』」
刘玄德:沈钞本、清钞本避清帝讳改作「刘元德」,今据元延祐本复原。以下沈钞本、清钞本凡讳字改「玄」为「元」者,径予复原不再出校。
「一任刘玄德,相对卧高楼」句:傅子立注:「《三国志》:『陈登字元龙。郭汜曰:「陈元龙湖海之士,豪气不除。」刘备问汜:「君言豪,宁有事邪?」汜曰:「昔过下邳,见元龙。元龙无客主之意,久不与语。自上大床卧,使客卧下床。」备曰:「天下大乱,望君有救世之意,而君求田问舍,言无可采,如小人,欲卧百尺楼上,卧君于地,何但上下床之间邪?」』玄德,备字也。」刘尚荣按引《三国志·卷七·〈魏书·陈登传〉》:「陈登者,字元龙,在广陵有威名。又掎角吕布有功,加伏波将军,年三十九卒。后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,表与备共论天下人,汜曰:『陈元龙湖海之士,豪气不除。』备谓表曰:『许君论是非?』表曰:『欲言非,此君为善士,不宜虚言;欲言是,元龙名重天下。』备问汜:『君言豪,宁有事邪?』汜曰:『昔遭乱,过下邳,见元龙。元龙无客主之意,久不相与语,自上大床卧,使客卧下床。』备曰:『君有国士之名,今天下大乱,帝主失所,望君忧国忘家,有救世之意,而君求田问舍,言无可采,是元龙所讳也,何缘当与君语?如小人:欲卧百尺楼上,卧君于地,何但上下床之间邪?』表大笑。备因言曰:『若元龙文武胆志,当求之于古耳,造次难得比也。』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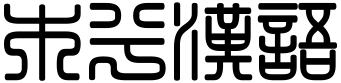
这首词上阕咏史,写东晋谢安的经历,意在「以不早退为戒」,下阕述怀,设想早日「退而相从之乐」。这首词表现了作者隐退的决心,不希望被世间的功名利禄所束缚,也表现了兄弟二人手足情深。
上阕咏史,写东晋谢安的经历,意在「以不早退为戒」。发端明点「安石」,领起上半阕。词人的写作角度比较独特,既不写他经天纬地的才能,也不写他建功立业的辉煌,而是写他人生的另一侧面。劈头就写谢安中年出仕的尴尬:他本来隐居会稽,踏上仕途时鬓发已开始染上秋霜,令人吃惊。再写人情的难堪:人到中年,与亲友相别时觉得难舍难分,于是借音乐来抒写离愁。而后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愿:「一旦功成名遂,准拟东还海道」。语气多么肯定,多么坚决,确实是对史书中所谓「安虽受朝寄,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,每形于言色」(《晋书》)数语准确的表述。而结果却是「扶病人西州」,这就反跌出困于轩冕不遂雅志的「遗恨」。这种「遗恨」,便是作者引出的鉴戒——「不早退」。词中的「困轩冕」只是一个文雅的或婉转的说法,实际上(至少在某种程度上)与贪恋功名富贵是联系在一起的。
下阕述怀,设想早日「退而相从之乐」。换头「岁云暮」三字承上转下,「岁暮」当指年华老大,「早计」是对「遗恨」而言,其内容便是「要褐裘」,亦即辞官归隐,过平民生活。以下七句是由此产生的设想:在归乡的千里长途中,每逢山水名胜或有贤主、良朋接待之类好的去处,可以随意逗留,尽情游乐,不必如官场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局促,一层:我带着醉意唱歌时你跟着唱和,我因醉酒倒下时你要搀扶我,——只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怀得失的,二层:这样,有雄心大志的人会瞧不起我们,那就悉听尊便好了,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,三层:这种种设想,情辞恳切,言由中发,有如骏马驻坡,不可遏止,充分表现出词人对辞官归隐而享弟兄「相从之乐」的夙愿。「我醉歌时君和,醉倒须君扶我」,极写想象中「退而相从之乐」的情态,简直是对二人的「合影」。篇末「一任刘玄德,相对卧髙楼」两句,反用典故,并非真要趋同胸无大志的庸人,而只是强调素愿的坚定不移,这体现了用典的灵活性。
同《南乡子·东武望馀杭》、《醉落魄·分携如昨》、《减字木兰花·贤哉令尹》等词作一样,这首词着重表现了东坡前期思想的另一面,虽然「功成名遂」尚未实现,出仕思想仍占上风,但在某种程度上徘徊于出处之间,却是可以肯定的。早在嘉祐五年苏氏弟兄寓居怀远驿时,即有「夜雨对床」,「为闲居之乐」(苏颍滨《逍遥堂会宿二首》引、《再祭亡兄端明文》等)的口头约定,这一回正是对前约的重申,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其弟的安慰,词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。不过,他在诗词中不断表达的这种归卧故山的雅志,最终还是没有实现。苏颍滨词中的「但恐同王粲,相对永《登楼》」,倒成了他们此后生活的写照。